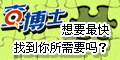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经济》杂志1月号
采访/本刊记者卢波摄影/本刊记者张朋
这件事牵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几乎所有国内大城市里至少上百万户人的利益。他们或者是他们父辈的私房,在1958年被国家统一“经营租赁”。在其后的很多年里,他
们中的很多人成了住房极其紧张的“特困户”,甚至无处栖居,流落街头。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突然发现,曾经被国家“经营租赁”的祖屋,其所有权其实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换言之,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要求把本属于自己的财产发还给自己,或者至少,对这些长期被占用的财产给出某种补偿。于是,他们开始了讨回祖屋的行动。这注定是极其艰难的行动。有关返还他们祖屋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只是在南方沿海一些地区“开”了一些“口子”,全面的政策出台以及法律上的确认,尚未见出端倪。这件事的历史背景和目下态势,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顿挫、坎坷,也预示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可能的前景。
讨回祖屋行动
“经租户”们讨还祖屋的勇气大都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权”之后才逐渐唤起的
1924年11月,冯玉祥麾下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废止优待清皇室条文,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皇宫。34年后的1958年,这支军队的参谋长陈琢如将军在北京的房产被新政权收归国家租赁经营。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的这种产权转换方式的正当性从未遭到过质疑。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
西北军参谋长陈琢如将军的长子陈松先生是最先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发生的产权转移的人之一,时间是在2003年深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强调尊重公民私有财产之后。陈松不久前向北京市房管局提出,应当将产权仍然属于陈氏家族的两处“经租房”发还给他。
长期埋藏于历史和话语地层深处的“经租房”问题一旦被发掘出来,人们就发现它身上纠缠了巨量的历史和现实利益。与陈松具有同样遭遇、同样意识并采取了同样行动的“经租户”目前在北京已有200多户。而那些因为同样的历史原因而有同样遭遇、只是目前尚未萌生足够产权意识的“经租户”在北京最少有24万之多。
在上海,在广州,在武汉……这些大城市里,这样的“经租户”的数量都要以十万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目前都在以各种方式讨要自己的房屋产权。
“经租房”的前世今生
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他到现在才提出发还“经租房”的要求,而不是在“文革”之后就提出这个要求,陈松先生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表白:“哪儿敢呐,那会儿!”
所有“经租房”问题的形成都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为了解决城市住房紧张,中央政府决定将城镇居民手中超过一定面积的私房强制性地收归国家“经营租赁”,此即所谓“经租”。
在北京,有24万户居民的私有房产被“经营租赁”,原因在于他们的住房面积超过了225平方米,而不少城市贫民却连1平方米也没有,大雪天也住在窝棚里。在中国人的传统财产观里,政府的这种改变产权归属的做法无疑是正义之举。
“经租户”们都有着大体类似的经历。“经租户”梁景禄的父亲解放后在北京东华门一带经营餐饮业,赚到一笔钱后,就在东四买了两处房产。当时,投资房产被称为“吃瓦片”。梁家两处房产分别是1956年冬和1957年初买下的。没住上两年,1958年的“国家经营租赁”政策开始实施,梁家因房子面积累计大于225平方米而被收归国家经营租赁。
梁景禄先生分析说,当时卖房子的人可能就已经听到风声,才把房子卖给他父亲。梁父眼看半生积蓄换来的房产转眼就被国家“经租”,懊悔莫及,不久郁郁而终。
“文革”开始,局势又为之一变,“经租户”们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1966年,陈松先生被红卫兵“扫地出门”,1978年才回到北京,虽然他家在北京有好几处房产,他自己却没有地方住,多亏下乡时的朋友收留,否则就要流落街头。他向房管所提出的发还一间房自己住的要求被拖了好几年,在1985年才得到答复。当时,房管所表示可以将他家的一处房产发还给他,但是希望他将自住部分之外的房产出卖给房管所,陈先生没有多考虑就同意了。陈先生对《经济》记者说,那个时候,谁敢提什么产权,敢跟国家讨价还价?将近200平米的房子卖了4000多元,现在看来是亏了,当时只觉得谢天谢地,国家拿走房子还能给你点钱,已经相当不错了。
今天的陈松先生已经习惯把“产权”两个字挂在嘴边。他对《经济》记者说,最好是能够把他家原来的房产原封不动发还给他,怎么处置由他自己决定;即使政府不能将房产原样发还,而是给予一定补偿,每平方米补偿的金额也不应该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应该由双方协商决定。
和陈先生一样,“经租户”们的勇气都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之后才逐渐培育出来。今年已经80岁的戎权秀老人是“经租户”中仅存的当年亲手办过经租手续的人,她说,没想到还真能赶上这好日子口,活到能向政府说上话,商量要回祖屋的这一天。戎权秀的老伴死在红卫兵手里,私房的事她20多年来一直讳莫如深,现在也加入了“经租户”要求发还房产的行列。
现代产权意识的萌生或回归
搜检历史,人们可能会发现,现代产权意识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购房置地是中国人的老传统,这个传统甚至穿越意识形态顽强地生存到解放后。记者在采访中吃惊地发现,直到1957年,北京仍然存在地下房地产交易市场。前文提到的“经租户”梁景禄的父亲在东四的两处房产,就分别是1956年冬和1957年初买下的。
“购房置地的传统”在1958年开始断裂。这一年,城镇居民手中超过一定面积的私房开始被强制性地收归国家“经营租赁”。通过住房使用权的转移,暂时解决了当时城市住房极其紧张的问题,让一些城市贫民获得了安身之地。但是在国家投资向生产资料领域倾斜,住房基数不变的情况下,私有房屋使用权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十几年过去,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殖,城市住房狭窄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峻。据建设部房地产业司杨家燕副处长提供的数据,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仍然不到3平方米。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一定对好几户人家、几十口子合住一个小四合院的情景记忆犹新。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改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居民住宅的竣工面积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2002年底,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2.79平方米,北京也达到了人均18.2平方米;同时,城镇住宅自有率达到72%以上。请注意,这两个数据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城市居民住宅的投入并没有增加多少,而居民住房竣工面积却以几何级数增长,城市住房状况大大改善。原因在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居民住房需求拉动的住房投资已经占到了城市住房建设总投资额的90%以上。
2002年一年,全国个人购房支出总额就达到8000亿元,个人购买商品住房占商品住房销售额的比重达到了95.3%,居民住房支出已经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真是“形势比人强”,曾经被人为割断的历史现在又开始延续,私人产权又成为了一种现实。现在商品房出售的一个重要程序就是通过签订明确的合同,保证为业主办理产权证,承诺业主对房产拥有不可剥夺的权益。建筑业能够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城市居民情愿把积蓄中的大头拿出来购买商品房,关键在于他们相信,自己的房产再也不会被轻易剥夺掉。
这种信心感染了那些历尽劫波的“经租户”,支撑着他们如今讨要祖屋的行动。
契约精神
北京的梁景禄先生等来了宪法重提保护个人财产的这一天,希望能够要回祖产,以告慰先父。而实际上,经租户要求发还房产的历程几乎就是一部民间产权意识逐渐复苏的当代经济思想史。经租户的维权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武汉市江汉区居民胡晓久是记者接触到的案例中第一个提出发还经租房产权的人。
胡晓久向记者叙述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维权历程。1981年,已经30岁的他住在自己家原来私房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由于没有房子,一直没能结婚。当他听说房管所要把自己家的私房重新调整,分配给本所的职工,他就冲下楼来撬开房门,抢占了其中的一间。
江汉区房地产公司就此以抢占公房的罪名将他告上法庭,没想到却为胡晓久提供了一个申明自己意见的机会。胡晓久提出反诉,指控江汉区房地产公司非法侵占私人房产。胡晓久告诉记者,以当时的法治环境,如果是他自己提起对房管局方面的诉讼,肯定不会被法院受理。
第一次开庭富有戏剧性,胡晓久在法庭上说,他完全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他只听说过生产资料改造,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活资料也要改造。他家的房产是自住房,从来没有出租过,没有生产活动,被纳入国家经租房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法官说,哦,原来你的房子属于生活资料,那要请江汉区房地产公司把情况调查清楚,当即宣布休庭,继续调查。
第二次开庭,房地产公司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指认胡晓久的父亲为资本家,他家的情况属于资本家改造,所以生活资料也应该纳入改造范围。胡晓久在法庭上辩称,他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划定的成分是小手工业者,1955年公私合营中,以劳动者身份加入了合作社,用什么样的标准也谈不上是资本家。
法庭合议后,认为胡晓久的房产确实属于错占,是经租扩大化。但是“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情况”,不宜由法院对这种情况作出明确的判决,要求双方庭外和解。江汉区房地产公司发还了胡家的部分房产,并达成口头协定:一旦国家有发还经租房的政策出台,江汉区房地产公司将立即发还胡家的全部房产。
胡晓久现在能做的事就是,在提倡保护私有财产的大环境下,等待政府出台一个关于经租房的明确政策。
在北京,政治觉悟相当高的市民们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论述中看到了寻回自己房产的希望。梁景禄先生首先发现了“经租房”政策中的漏洞。他告诉《经济》记者,1958年政府和经租户签订的合同,根本没有涉及产权变更!
由于绝大多数经租户的合同文本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他们能看到的合同都是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政府一方的合同。经过查询,梁先生发现这个合同没有任何涉及产权问题的词句,只是谈到了租金问题。合同原文为“由国家经租,即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现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梁先生说,合同称经租户为房主,可见当时是认同屋主的所有权的,只是租赁权和使用权的分配归国家。
“经租户”们到北京市房管局反映情况,得到的正式答复是“根据1964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房屋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国房字21号)的规定,最高法院(64)法研字第80号《关于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丧失所有权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是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为此,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国家租金,不能收回由国家经租的房屋……”
梁先生对此表示不解:为什么高法80号批复提到“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而当时房主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文本上却只字未提产权变动。高法的这种解释依据何在?
经过查阅历史文件,梁先生获悉,高法80号批复的惟一依据的是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一份文件《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出要将城市中房产较多的居民的私房进行赎买。但是政府在1958年与经租户门签订的合同中却根本没有提“赎买”产权一事。
梁先生告诉《经济》记者,执行经租政策的当事人已杳如黄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既然早在1955年已经决定“赎买”,却没有在1958年的合同中向当事的另一方声明,或许是出于工作方便,避免遭到剧烈抵制。能看到这份文件,了解政府方面真实意图的绝大多数已不是当事人,而是他们的后裔。从商业意义上讲,这是一份典型的不规范合同。
梁先生认为他们的房产在当时是合法的,谁也无权剥夺。他告诉记者,当时仍然生效的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按照那部《宪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没收公民的合法财产,更不能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继承权。
梁先生找到了合同上的明显漏洞,但其他城市的经租户却未必有这样的幸运。北京市1958年执行“经租”政策多少还履行了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政府出面核定住房面积,与房主签订合同。在武汉,由于当时的执政者任意扩大经租范围,经租手续草率,甚至不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更为普遍。
上文提到的胡晓久一家在江汉区吉庆街金兰巷拥有一套两层小楼,总面积300多平米,1958年8月,街道干部强迫他父亲填写了私房改造规划表,签报表,然后由“吉庆街道群众”名义发给他家一份改造协议,将全部房产收归国家经营租赁,定息10%,楼下部分租给别人,楼上“租给”他们家自住,他家应付的租金和楼下住户的租金互相冲抵,所以街道上不付分文就“赎买”了所有房产。1964年“四清”时,根据国家经租房不得自住的规定,他们家十几口人被赶下楼,在旁边搭建的房子里住到“文革”结束。
武汉市江汉区居民朱惠芬向记者反映,他父亲是在湖北省轻化公司工作的普通知识分子。1949年以前凭劳动所得修建了一座三层楼的砖木结构的私有住房,位于武汉市洪益巷91号,房子完全供自家居住使用,按时缴纳房屋的天地税,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然而,1958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运动中,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盛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1958年7月5日,一张“红喜报”将她家的房子强行占有,收归国家经营租赁的行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只是在她家大门口贴上了那张“红喜报”,产权交易就算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朱惠芬女士不断与房管方面交涉,1990年11月20日,江汉区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报经武汉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审查批准,撤销了1958年的错误改造,拿出的解决办法是:除原业主自住二楼4-6号房已作留房外,其余他人租住的125.55平方米,按每平方120元作价收购,不能退还产权。朱惠芬女士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她提出,国家颁布的《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那么地方政府是否有义务遵循这个通则呢?既然政府已于1990年11月20日批准撤销改造,理应依法返还财产,恢复财产权,发还给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在业主一直不同意收购的情况下,单方面制定价格,强行收购显然是违背《民法通则》,违背契约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