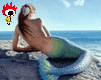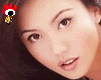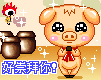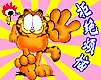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姚洋
我们正在向意识形态告别。进大学已经不必考政治,大学生不再谈论国事是非,网络上充斥着商业炒作,电视台频频出镜的是俊男靓女;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扎扎实实地挣钱,快快乐乐地享受。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正在走向市民社会。对于一个习惯了皇权和僵硬的教条的民族来说,这个变化来之不易,因此就更值得我们珍惜
。
在制度方面,中国也正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无特殊情况下,农户的土地不得进行调整;同时,农户的土地可以继承,土地使用权可以永久性地转让。这样,农村土地所有权就基本具备了私有产权的两大特征,即排地性和可转让性。因此,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继土改、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第三次土地革命。在城市方面,大规模的企业改制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对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而言,改制的实质是民营化,“国退民进”是许多城市的改制口号。许多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变成了私人企业,企业职工变成了私人企业的雇员。当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时候,职工动辄上访;当变成私企雇员之后,他们反倒安分了许多。所有权就有这样的神奇力量:既然企业是别人的了,除了应得的报酬,其它想法就都是非分的。企业改制属于那种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因此,尽管其程度不亚于任何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竟然没有多少反应,就连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话,也不会对此有多少察觉。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已经在九十年代悄然地完成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轰轰烈烈但结果惨痛的经济转型。
中国人民曾经饱受意识形态之苦。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不得不在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下生活,哪怕是边远山村里的一个老农也要早请示、晚汇报。这样强加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天就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激励着每个人暂时放弃了对自我利益的考虑。但是,人们的热情很快就被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所烧灭,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把意识形态变成了迫害他人的工具。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无疑是一场失败的试验;但是,如果从对普通人的生活和自由的束缚来看,则计划经济时代僵硬而多变的意识形态比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还大。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比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低,同时又在教育、卫生和妇女解放等方面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因此,计划经济的三十年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僵硬而多变的意识形态给我们留下的,除了痛苦的回忆和今天仍然可见的不良影响,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务实取向意义非凡,正是这种取向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民社会。然而,在旧有的意识形态失去影响之后,一个适应于市民社会的新意识形态却没有建立起来。当意识形态褪去的时候,利益就成为一切的主宰。对于个体而言,这可能仅仅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你可以选择沉湎于物质享受,也可以为人类的命运暗自神伤;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时下最好的反面教材是前苏联国家。当戈尔巴乔失开始他的“公开性”改革的时候,前苏联就开始出现一批由官而商的寡头;当前苏联于1991年解体的时候,这些寡头迅速地控制了俄国的金融,成为金融寡头。他们的权势如此之大,连俄政府也要让他们三分。不仅如此,一夜之间形成的民主政治为这些金融寡头控制国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国家机器被他们挟持了。尽管存在一个名义上的民主机制,国家却实际上控制在少数寡头的手里。
如果把俄国的政治比作滑坡,印度的政治则是慢性自杀。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中央集权国家。到1947年独立时,民主似乎是统一印度的唯一可接受的选择。然而,由于人口和民族的过度分化,在这样的民主框架下所形成的任何决策都是彻底的妥协,结果往往是社会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印度的国有企业不多,但亏损严重。因此,当右翼政党执政的时候,政府就要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意味着裁员,工人们就要失业。这时,在野的左派政党就领着工人上街游行,私有化因此不了了之。然而,当左派政党执政时,政府也要私有化,因为国有企业的亏损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左派政党已经把它的意识形态抛在脑后,而完全被利益所左右。更有意思的是,此时在野的右翼政党却反过来反对私有化,也领着工人上街游行,私有化又不了了之 。右翼政党也不顾自己的意识形态了,一心只想和左派作对。
既使是最彻底、最自由的民主社会也需要建立在最基本的公民共识之上。在阿富汗战场进展不畅的时候,英国的一些国内报纸开始批评布莱尔紧跟美国的政策,有人甚至怀疑英国参战的正义性。布莱尔的发言人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说:“英国是一个知道对错的国家。”我们尽可以指责美国的人道主义干预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而行其霸权主义之实,但是,美国的人道主义干预总体上却得到了国内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是美国社会的共识。美国社会有一套明确的价值观,而这套价值观又同时体现在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上,哪怕这种体现是字面上的,它也达到了争取民意、获取民众政治认同的目的。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优于俄国和印度。我们没有经历俄国那样的巨变,也没有印度那样分散的利益集团,过去二十年的历程表明,作为民意最广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过了一条基本正确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的成功,部分源自于由计划经济的失败所创造的创新空间。必须看到的是,这个空间到今天已经变得非常狭窄了,进一步的变革必然要更多地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利益更可能变成驱动各级官员的主导力量。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倾向。
中国政府架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的财政分权和高度的行政集权并存。适度的财政分权对调动地方积极性有正面的作用,这是毛泽东早在1957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已经指出来的。但是,过度的财政分权则可能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问题之一是地方公共品提供不足。目前的财政分权已经到达县一级,各县独立负责本区县的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和医疗保险也只能统筹到县一级,而保险的正常运行依赖于保险的覆盖面,覆盖面越大越容易进行,目前高度分割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教育。教育的日常开支是全部由县级政府负担的,对于富裕县来说,尚不成问题,而对于贫困县来说,则成为大问题,因为有一些县60%的财政支出花在教育上。教育是立国之本,可惜我们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共识。
过度财政分权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地方政府行政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每级政府的目的都是减轻自己的负担,增加自己的收入;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矛盾的逐级下放。为什么乡镇一级政府人满为患?就是上级政府矛盾下放的结果。大、中等毕业生,特别是农林、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要分配工作,省、市、县都不要,乡镇只好兜底。军人转业安置也是一样。乡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近年来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拥有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来说仅仅意味着负担,因此,企业便逐级下放。县级以上的政府只抓住少数效益尚可或可以卖掉的企业,大部分企业则下放给了区县一级。对于改制企业,几乎所有城市都要求新的企业接收全部原厂职工,无论原厂的臃员有多少。为了平衡新的管理者的利益,各个城市在资产方面大打折扣,以极便宜的价格把企业资产卖给新的经营者,而新经营者能否兑现不解雇职工的承诺则不在近期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做法看似解决了问题,实则是下放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矛盾会重新暴露出来。比如,某市一国企的新经营者将企业卖给另一家企业,后者接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
过度分权的弊端和中国高度的行政集权有关。一方面,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绝对的权威,可以要求下级政府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行政很少受来自底层的监督,两方面的迭加造成各级政府行政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财政架构决定了她的政府架构;更进一步,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是她的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不在于国家说它是什么,而在于国家财政支出的流向。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情形不容乐观。自1994年实行分稅制以来,财政支出在各省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一些以烟、酒业为经济支柱的落后地区甚至成了财政净输出地。时至今日,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收入转移机制,中央对地方的拨款不是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发放,而是以投资项目的形式发放。由于投资项目一般要求地方的配套基金,发达地区自然要比不发达地区具有优势。这样的财政支出方式不是缩小,而是放大了地区差距。
市场已经被证明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机制,但是,市场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近些年来,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批评计划经济的弊端方面,哈耶克无疑有卓越的洞见;但是,他的一些观点被国内知识界进行了不恰当的引申,表现之一就是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比如,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就税收以及地方官员之间就升迁所展开的竞争就足以约束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和社会效率相吻合。但是,市场的竞争原则恰恰不适合于政府。市场要求每个参与者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对于政府而言,恰恰是不能只最大化参与者的个人利益;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由此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政府是为公共利益而创立的,因此它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政府行为的商业化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把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归咎于政府官员的理性并因此而容忍是没有道理的。理性可以是一个研究者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工作假设,但此时得到的只是关于“现实是什么样”的实证性结论,而不解决“现实应该是什么样”的规范性问题。同时,尽管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制度设计有关,如垂直行政和财政分权之间的矛盾,但是,制度也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来回答下面这样的问题:公民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社会分配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分配?对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言,回答这两个问题是维持其政治性统一的前提条件。走向市民化的中国也在同时走向多元化,这个过程已经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的恐怕不是代表性的问题,而是如何为民众提供一个公正观的问题;这个公正观应该向民众展示一个理想社会的图景、一个判断社会分配好坏的标准和一套适应当代世界的价值体系。
乌托邦不是现实的存在,但是,乌托邦中包含着人类美好的追求。在经济日益市场化、社会日益市民化的时候,务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放弃理想。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将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家将是一盘散沙;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必定注重眼前的蝇头小利,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家就会变成少数人捞取私利的工具。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冲破了旧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民众的认知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现在是建立新的理想的时候了。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