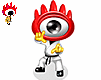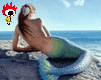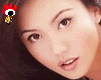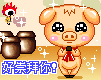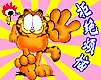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31日 16:33 中评网 | |||||||||
|
姚洋 约翰.里德(John Reed)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此之前,他是左翼杂志《群众》(The Masses)的一名记者。一九一七年,他和他未来的妻子路易丝.波南特(Louise Bryant)一道来到俄国,亲眼目睹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们为俄国的巨变而感到振奋,向美国发回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稿件。回到美国后,他出版了影响巨大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
以上是电影《约翰.里德》的主要内容。今年夏天,在位于日本新泻乡下的一所大学的教师宿舍里,我在深夜看完了这部电影,感慨良多。有人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如果不激进,那么他的心智有问题;但如果他在三十岁之后还激进,他的头脑就有问题。”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意气风发,疾恶如仇,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改变世上的所有不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到处碰壁,这才意识到:“我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语)所以,他开始不那么左倾,而转而注重理智地“思考”,从离经叛道的青年变成忠实地捍卫主流社会的一分子。 里德的同志、《群众》的主编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就是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三十年代之前,伊斯特曼是苏联和工人阶级事业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不义之战,因此坚决反对美国参战。当美国最终于1917年对轴心国宣战之后,《群众》杂志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批评。此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昂,左翼势力迅速上升。威尔逊政府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玛(Mitchell Palmer)和他的特别助手、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乘机向美国公众渲染“红色恐惧”(the Red Scare),并对美国的左翼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镇压。于1917年通过的《反谍法》是他们手中的一件有力的武器,《群众》杂志以违反《反谍法》为由遭到当局的起诉。虽然对《群众》的指控两次都被陪审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定为无效,但是杂志不得不关闭。伊斯特曼又和几个同志一起创办《解放者》(The Liberator)杂志,继续左翼宣传。但是,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迫害使得伊斯特曼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先是变成托洛茨基的忠实支持者,在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后,又变成社会主义的强烈批评者。他因此被美国主流杂志《读者文摘》聘请为主编,并在该杂志上发表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伊斯特曼更是变成了麦卡锡的忠实支持者,他的文章对麦卡锡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伊斯特曼还是极端的例子的话,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狂风骤雨的许多美国人的转变则是普遍现象。我的导师便是其中一个。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所有高中生都必须抓阄决定是否要上越南战场。轮到我的导师一届时,正好越战结束,他因此逃过一劫。他的本科是在乔治城大学学外交,毕业时到美国国务院应聘,得到的评价是:“此人爱思考,不适合做外交工作。他应该去搞研究。”由此他便决定到威斯康星大学学发展经济学。七十年代末,他以研究拉美土地问题开始学术生涯。拉美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土地占有的极度不均,少数的大庄园主和多数的无地农民形成鲜明的反差。因此,几乎所有的拉美知识分子的思想都左倾。导师也不例外。他在书架上摆放的一本他自己用西班牙文写的书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虽然不懂西班牙文,但从封面上高举拳头的愤怒的农民我也能看出,这是一本关于拉美土地斗争的书。他的太太是律师,是那种天性开朗和豁达的美国人。俩人结婚近二十几年一直都只有一辆车,导师无论雨雪,上、下班一律骑自行车。他也从来不打高尔夫球,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爱好。然而,最近他来中国,告诉我说,他们新买了一辆BMW,第一次拥有了两辆车;同时,他也开始和太太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了,并发现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尽管他的学术取向仍然左倾,他的生活却已经逐渐中产阶级化了。 如同波斯纳所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多数情况下只是把自己关在学术的象牙塔中,无非偶尔露一下面,做一回公共知识分子而已。他们并不真正参与公共事物,他们的公共讨论只是他们偶尔从象牙塔中的探头张望;很快,他们就会把头缩回去,继续和社会保持距离。苏力很有勇气地自我认同波斯纳的观点(《读书》2002年7月号),认为自己每次超出专业范围的活动也不过是从象牙塔中探一次头而已。曹锦清怀着一个都市知识分子渴望了解黄河边上的中国的心情到河南采风,希望以客观的学者的眼光洞悉中原腹地的文化嬗变。然而,《黄河边的中国》与其说是一部学术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注解颇多的游记,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经世济民的理想。曹锦清并没有信守学者不参与的规范,而是在多个场合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当他慷慨激昂地在黄河北岸的小村庄里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已经脱离了学者的角色,而担当起启蒙者的任务。他的激情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回报,在他临走的时候,村民纷纷前来送行。然而,参与的激情也只能在那种特定的场合下才能释放;回到上海之后,曹锦清仍然是一个学者。 我也一样。一九九九年我到广东东莞一个村庄调查外来移民的情况。村里有许多外资工厂,打工者几乎都来自内地省份。一天,我在一个工厂里召集工人填调查表。来的工人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女工,许多人小学都没有读完,根本无法填写,只能让他人代劳。但其中一个女孩填表的速度极快,原来她已经读完高二了,因为家里没钱而辍学。填完表之后,她就对我诉说起自己的遭遇来。她家在河南,喜欢唱歌,唱得很好,但父亲就是要让她辍学,因为家里没有钱供养她。没有办法,她于一年前带着200元钱和朋友一起来广东打工。她说着便哭了起来:“我就是想上学,想唱歌。你帮帮我吧!”我能帮她什么呢,除了心痛?领班过来大声地呵斥她,要她回去干活,她只好抹着泪去了。我无法忘记她转身看我的眼神,那是一种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而稻草又迅速断掉了的绝望。 我到村里的联防队去联系采访,发现厅里跪着一个光着脚的外地年轻人。联防队长告诉我,他是小偷,昨天夜里被抓住的。年轻人面容佼好,如果生活在城里的富足人家,一定是许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此时,他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只会说:“我不是小偷。”联防队长是一个极负责任的人,他捡起年轻人的一只鞋,开车带着我去看昨夜抓到他的地方。原来,一个工厂宿舍连续发生盗窃案,昨夜又发生了一起,但联防队赶到时,小偷刚跑掉,还掉了一只鞋。队长认为小偷没有跑远,便埋伏下来等着。到深夜3点左右,小偷觉得安全了,从躲藏的草丛里出来,被抓了个正着。队长带我去看小偷留下的鞋印,把那个年轻人的鞋一放,果然对上了。 除了夸奖联防队长工作认真、为民锄害,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我能告诉他,体罚犯人是违法的吗?我能建议他给年轻人一点尊严,因为他偷窃可能是出于生活所迫吗?都不能,因为我是一个需要联防队长带领进入这个村庄社会的旁观者。 一位社会学家在评论完我的一次学术演讲之后对我说:“经济学家真厉害,对什么事都那么冷静。”的确如此。十几年前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一起游三峡,船过一处码头时,恰逢一艘运煤船在卸货,一队搬运工扛着沉重的煤袋爬几十级的台阶把煤从船上卸到高高的岸上去。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说:“怎么这么落后?为什么不用传输带?”我回答说:“用了传输带这些工人不就没活干了吗?扛包挣钱总比失业好。”不是我没有怜悯心,而是事实就是如此。现在,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时常以这个例子做为一个问题,看学生是否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在要求学生放弃道德考量,而专注于经济学的“冷静”思考。 尽管心中有无限的正义冲动和经世济民的抱负,作为学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说到底应该还是社会的旁观者,因为社会分工要求学者对社会进行公正、冷静和深入的分析。十几年前在北大做研究生的时候,北大校报上登了一篇学生来稿,说北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方面不如清华学生,作者因此呼吁学校多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当时我就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北大就是应该培养思想家。近年来,北大步清华后尘,在学生中间开展创业竞赛,团委还拨专款资助那些有希望的项目。看来,在社会实践方面赶超清华仍然是北大的理想之一。但是,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北大是没有必要和清华在培养实用型人材方面一比高低的,北大应该培养学者(思想家是培养不出来的,但学者中间可以出思想家),因此,北大不妨和社会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这当然不是要求北大培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一个学者可以不参与社会,但必须关注社会,洞察社会变化后面的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的氛围中生活得太久了,许多人的学术研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对“主义”的诠释和主张式的呐喊。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听到最多的是:“我的观点是……”“我的主张是……”可是,你的分析在哪里呢?说实在的,要谈主张,学者大概不会比地方干部强多少。最近到南方一个城市调查国有企业的改制情况,发现当地经贸委主任的主张比我们许多教授的主张更开放、更符合实际。他给我举例说,在一次会议上,他辩倒了一位教授。那位教授主张,像公用事业这种行业还是国家经营好。经贸委主任反问:“为什么?香港把公共汽车线路租给私人经营不是很好吗?我看象水电、煤气这样的公用事业也可以照此办理。”我们的教授无话可说。我想,这位教授大概只会谈主张,不会分析,否则,他至少可以说出几条过硬的理由吧?当主张代替了分析的时候,学问就变成伪学问了。这样的学问,不如不做的好。 保守的意识形态容易被识别,也容易在分析面前败下阵了,比较难识别的是隐藏在分析之下的意识形态。在目前的中国,价值中立是学者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一些人更是愿意以价值中立自居。表现在经济学界,就是滥用经济理性的推理,而忽视社会的其它价值。比如,江西发生了巨大的鞭炮厂爆炸事件,可死难工人的家属却劝政府要继续允许办鞭炮厂。于是,有人就会说,工人是理性的;言下之意,鞭炮厂恶劣的作业环境并不需要改变。但是,对工人来说,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家里等着没饭吃,另一种是到危险的鞭炮厂工作。在前一种选择下,他们可能只能等着饿死,在后一种选择下,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两相权衡,选择后者当然是理性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工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在没有选择下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理性的,但导致这种选择的外在制度安排及其实施过程却是不人道的。人不是只会搬运牛粪的屎壳郎,经济追求只是他的所有追求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必须认同这一点,保护和鼓励人的崇高的一面,而不应该把公民降低为在极低的水平上为生存而奔波的昆虫。事实上,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做好工厂的安全防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国家也有较完备的安全生产法规,问题出在地方政府的管理和企业主的执行上。不可否认,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地方政府往往偏向于后者的利益,因为后者为地方带来就业和税收。在这种偏向于资本的权力格局下,工人的利益经常被忽视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很多情况下,许多人强调经济理性不过是在给他们偏向资本的意识形态穿上一件价值中立的外衣。要知道,完备的理性和经济学定理只出现在教科书里,而并不完全反映真实世界。但是,这一点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以为书本里的定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好比弗里德曼的名言所说的:“如果数据没有支持理论,则肯定是数据错了。”对书本知识的盲从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使书本上的定理变成一些人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基于理性的分析因此也变成了对自己意识形态的辩护。 所以,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学术如果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学者就和政治鼓动家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言,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根本不相容。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人阿玛蒂亚.森是主流经济学家中极少数公开表示自己在政治上是左派的人。最近,趁他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我问他是如何处理他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的。他回答说:“我的政治立场当然对我的学术研究有影响,我之所以选择研究饥荒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左倾的政治立场。但是,一旦问题选定,我们就必须用客观的态度来进行分析。我在对饥荒的研究中采用的完全是主流的新古典方法。”森的这段回答,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搭起了桥梁:作为知识分子,一个人要拥有、并积极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他是入世的;作为学者,一个人则要搁置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客观的态度来对社会现实做出分析,因此他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学者总是处在入世与旁观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美。一幅好的艺术作品需要张力,一个好的理论也需要张力,丰富的人生本身就体现张力。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边界的穿越者,是入世者和旁观者的统一。 然而,这样的要求可能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苛求。成就彰著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他过去二十年的学术生涯是在理论研究和现实政策讨论中交替度过的,而八十年代中期参加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使他受益非浅。中国没有这种条件,官与学之间的联系永远是单线的,要么由学而官,要么由官而学,决不会出现象克鲁格曼那样官学交替的情况。一个学者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想法,就必须向官靠拢,或干脆自己做官。那些不想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的人,则成了书斋里的隐士。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不仅可以在报刊上和广播电视上发表他们的主张,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参加街头群众运动。中国没有容纳这种参与的空间。学者们也上电视,但谈的是经济形势、房产信息以及股市行情,而不是思想。这决不是电视台的商业化倾向所能完全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还有待时日。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姚洋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