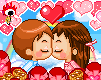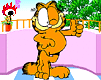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抵抗SARS:增强社会免疫力的改革良机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2日 18:21 中评网 | |||||||||
|
传染病将卷土重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忽然让人们感受到疾病对健康、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秩序的威胁。20世纪后期,人们在和传染病的斗争中似乎已经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以至于1969年,美国外科大夫william Stewart在国会发言时指出:“ 应该合上关于传染病的书本。对抗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然而,这种观点过于乐观了。其实,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姆.麦可尼(Will
历史学家们发现,在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中都找不到人类社会持续进步、后人的生活水平会比前人更高的观念。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瘟疫的爆发。瘟疫使得人口数量无法持续增加,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提高。大规模的瘟疫爆发甚至影响到历史的演进,瘟疫影响到战争的胜负、王朝的兴衰和文明的灭绝。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4-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1348-1349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黑死病几乎传遍欧洲,有1/3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猝然降临的灾难。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也往往发生在瘟疫肆虐的时代。历史上两次主要的瘟疫爆发期,一次是在东汉末年,另一次是在明末清初。明万历、崇祯年间华北连续爆发瘟疫,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和后来清兵顺利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是乘虚而入。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 19世纪以来尤其是到二战之后,随着细菌学、流行病学的发展、公共健康体系逐渐完善,历史上曾经是横行一时、被认为是绝症的天花、肺结核、鼠疫等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一些迹象表明,21世纪传染病可能会卷土重来。 首先,即使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仍然在为害人类的健康。每年全球死亡人口中大约有1/4是死于传染病。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把艾滋病、腹泻、肺结核、疟疾和呼吸道疾病(如肺炎)列为5种主要的传染病,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数占死于传染病的总人数的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3倍。 其次,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宣布肺结核成了全球危机,因为肺结核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而且因为病毒对原有的药品产生抵抗能力,导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续增加。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无法幸免于难。1953年美国的肺结核病例为84300起,到1984年减少为22200起,但是从这以后肺结核病例开始以每年14%的速度不断增加。原有的一些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传染性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癌症病人人数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的新增癌症病人受到传染病菌感染。 再次,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最著名的当属艾滋病(HIV/AIDS)。2001年全世界共有大约3360多万艾滋病人,每年都会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相当于每天有一万六千多人被感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5到1/4的成年人为艾滋病人;1976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不断肆虐刚果、加蓬、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这种致命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达到50-90%。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美国影片《恐怖地带》更是将这种可怕的怪病渲染得让人不寒而栗;1976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费城一家旅馆聚会,1个月之后就有221名与会代表和当地居民得了一种酷似肺炎的病,后来被称为军团病。致病的元凶是嗜肺军团菌,主要寄生在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管道系统中,可经通风口无声无息地入侵建筑物内的每个房间;1997年香港发现一名男童死于本来是家禽才得的禽流感。这场禽流感导致18人感染,6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20多年内至少出现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 美国医学协会(IOM)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主要原因:(1)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2)我们消费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可能来自遥远的他乡甚至异国。在种植、采摘、加工、包装、运输、储存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如果出现污染,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疯牛病和口蹄疫是非常著名的例子。而在美国,近年来接连发生通过食品传播的传染病。污染源包括快餐店的汉堡包、学生餐中的草莓、牛肉肉馅、冷冻的肉块、早餐麦片等等;(3)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发达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下降,更容易被病毒击溃。城市化导致人口居住过度集中,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的贫民窟,卫生条件极端糟糕,成为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但是也是病菌最容易藏身的地方;(4)战争和自然灾害是瘟疫的催化剂。战争过后瘟神接踵而至,大灾过后必有疫情。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会进入城市或逃往其他国家,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5)农业灌溉、砍伐森林、砍伐完森林重新植树造林、都改变了携带病菌的昆虫和动物的生活习性。很多传染病的爆发都是因为生物习性的改变,比如疟疾的传播范围超越了热带地区就是因为带菌的蚊子活动范围扩大了;(6)静脉注射和不安全的性生活;(7)微生物本身也有进化过程,进化机制使得它们能够适应新的寄主细胞或找到新的物种作为寄主,它们会生产毒素,它们会破坏人们的免疫系统,它们会对药物和抗生素产生抵抗能力,而人们大量使用杀虫剂、抗生素,加速了病毒抵抗能力的发展;(7)永远都有冒险精神的人们进入热带雨林和其他人迹罕至的地方,并带回了很多人类原本未曾接触过的病菌;(8)20世纪中期人类对抗传染病取得的胜利使得大家变得麻痹大意,原有的防治传染病的系统逐渐衰落,公共健康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心血管病和癌症等“现代病”,疫苗的提供没有跟上,财政支持不够,人员培训和公众教育都落伍了。 科学带给我们的并不总是前方凯旋而归的喜讯,这次,它让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我们的对手就在我们的身边却不露痕迹,渺小得令人忽视但是却经常表现得比人类更聪明。 我们正在进入风险期 SARS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不过展示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SARS在中国带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不过是未来多种突发性危机事件降临之前的一次预演。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相比之下,它究竟会造成多大的GDP或外商投资损失甚至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SARS正在考验中国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 国内不少学者呼吁,应该尽早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过去也有危机应对机制,只不过随着政治和社会体系的演变,危机的性质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图1显示了新旧危机背后的体制差异。在旧体制中,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通过下级向上级汇报,而处理意见则由上级向下级逐级传达。国家控制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各个“单位”。过去的危机大多被定性为事故或“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危机的角色是中层干部,有时候加上技术专家。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时候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依托的是上下级间的科层制,使用的杀手锏是对官员的罢免和升迁。往往是上司雷霆震怒,下级雷厉风行,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非制度处理方式可能是打破官僚主义或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中,媒体并不参与,除了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公众对危机事件大多情况下并不知情。过去的危机处理可以被称为“决策模式”。政府假定公众只是政府政策被动的接受者:如果公众获益,则可以继续执行政策,如果公众受损,则考虑变更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方便地采用“试错法”解决危机。传统的单位制(如居委会)在城市里几乎覆盖了全体居民,在有灾害或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只要动员单位,反应很快、很有效。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人口的流动和信息的传播,危机和灾难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信心打击可以较容易地被限制在一个地区之内,再加上在人民崇拜超凡魅力领袖的年代,即使政府犯错误,只要适当地调整政策,政府的合法性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是,由于官僚体系中信息的向上传输和指令的向下传达都不通畅,可能人为地扩大灾害或危机的实际损失。比如,在60年代初期中国的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反而是中国粮食出口最多的年份。 SARS充分地显示出,危机的性质已经改变。这首先是因为体制发生了变化:(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的职能已经大大弱化,越来越多的群体游离于单位之外,比如在外企和私人企业上班的员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等等。如果我们还是采取传统的单位传达控制的办法,就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空缺。(2)越来越多的危机超越了地区甚至国界的限制,称为全球性的问题。SARS最初发现在中国,但是其传播和影响已经遍及全球。介入和关注这一事件的还有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的政府、外国游客、外国商人,甚至从海外媒体获得信息的普通公众。(3)信息在民间的传播以及媒体和公共舆论介入政治决策。在一个处处透风的现代社会,真相已经不可能只在体制内传达,刻意的隐瞒反而助长了谣言的泛滥和公众的恐慌心理。与此同时,媒体逐渐在真实信息的传播、政策效果的监督和反馈、甚至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4)在现代社会中,决策日益多元化。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危机对各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某些人是灭顶之灾,对另外的人则是意外之财。甲地的疫情可能已经控制,而乙地的疫情才刚刚揭开盖子。尤其是,考虑到对不同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同样一个危机事件会引起各方极为不同的反应。 由于体制背景的巨大变化,危机处理机制也会发生变化。如今的危机处理可以被称为“博弈模式”。从对危机的定义、到对危机的反应,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公众的反应。危机并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时间的事件,危机是全社会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一个特殊时期。危机是一场没有导演、没有剧本的戏,公众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从幕后走向前台。 由于危机的爆发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危机的处理涉及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些都使得危机变得更加政治化。在处理危机的时候,需要注意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两个方面。宏观政治涉及到政治家在危机关头的表现。这已经被视为政府在国际社会、新闻媒体、公众中的形象。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明确政府的立场,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稳定公共的信心,团结更多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对于一直习惯于在体制内命令和服从关系的各级官员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他们必须学会说服和解释,从政府出来的信息要及时、准确、前后一致、易于获得、直接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并且,最好还带有些人情味。微观政治涉及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政府应该迅速建立危机应对小组,提出清晰的思路和改革建议,保证信息传递准确及时、物资和人事的动员畅通无阻。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宏观政治层面上政府必须保持一个声音、一个形象、这样才能稳定民心,但是在微观政治层面,高度的中央集权并不适宜处理危机。危机过程中枝蔓丛生,发挥各级政府的权威和职责更易于调动其积极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官僚行政总是政策执行的基础,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工作方式仍然少不了日常工作中的磋商、谈判和说服。 危机是对政府的最严峻的挑战。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危机的蔓延和扩散,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国家能力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危机能够带来连锁反应。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方面的危机。一个火花会点燃另一个火花,甚至燃起熊熊大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都曾经看到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动荡的例子。最近的例子如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的是国际收支危机,但是由于国内的金融体系积弊已久,又酿成金融体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印度尼西亚,对危机的不当处理导致了国内的社会动荡,最终苏哈托政权也不得不下台。 对比新旧危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认清新危机的性质,才能够帮助我们共渡难关。 重塑公共卫生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否成功地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爆发和蔓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1)建立一套传染病监测体系,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出现异常数据或当有新的疾病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地预测和汇报;(2)当疫情出现的时候,要有一支精干的队伍亲临现场,调查疫情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随时提出对策方案;(3)实验室的研究迅速提供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的技术支持,在这方面,由于很多病情是在全球范围内流传的,需要各国之间密切加强合作;(4)流行病学研究应该对疾病爆发的前因后果、疾病的传染途径,尤其是疾病与人类行为、环境因素的关系做出分析,帮助公共健康部门在防治和控制疫情的时候科学决策;(5)加强人医和兽医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病菌从动物向人类传染的动向;(6)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健康体系,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支持、训练和装备公共健康工作人员、加强对公众的普及和宣传等;(7)要有一支高效的危机处理小组,在防治和控制传染病的过程中,要保证物资、人力和资金的调度畅通无阻;(8)有效的公共沟通和公共关系策略,和国内外媒体、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9)当渡过危机之后,应该对危机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做出科学评判,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10)对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问题,如病毒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态系统的破坏、食品和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等等进行前瞻性、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关的预案措施。 ——近20年来,中国的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公共健康状况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提高(参见表1)。1980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每千人)为42,到2000年已经降低到32。198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到2000年已经增加到70岁。但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其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系统做了调查,并根据健康改善、政府责任、医疗提供的公平性等做了排名,中国的排名为第144位,排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孟加拉国的后面。 表1 中国、印度和泰国主要公共健康指标比较(1999年) 中国 印度 泰国 婴儿死亡率(每千人) 32 72 29 经专业护理人员接生的婴儿比例 51% 75% 71% 接种麻疹疫苗的人口比例 89% 84% 87% 避孕普及率 83% 41% 74% 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 2.4 0.8 1.7 每千人拥有的医生人数 1.6 4.1 0.2 子女生育数 1.8 3.1 3.4 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Report,1999 世界银行负责领导中国健康项目的官员Jagadish Upadhyay指出,“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1965-1976年间应该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黄金时期。城市里的国有企业工人不仅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而且“单位”也会负担其退休之后的医疗费用。农村通过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他们在受到训练后以最低的花费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健康保健,并在农村发展起了世界上最广泛的卫生保健体系。改革之后,一方面,随着私人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加大改革和重组步伐、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逐渐减少。根据全国居民健康调查的数据,1993年有27%的城市人口未参加医疗保险,到1998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44%。其实,有一部分人口即使名义上参加了医疗保险,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兑现,因为提供医疗保险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企业的头上,而企业是否有实力负担职工的医疗保险,取决于其经营状况。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改革,原来的“合作医疗”体制逐渐解体。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不到10%。 改革之后,公共财政对公共健康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根据在北京、沈阳等地的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市级医院的经费中只有10%左右来自政府拨款,区一级的医院更少,大约只有5%。为了弥补政府拨款的不足,医院逐渐蜕变为赢利机构,更糟糕的是,公共卫生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化,医院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垄断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医院自然会普遍存在多开药、药费高、治疗费用高甚至医疗事故多等问题。目前大约76%以上的全国人口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自费看病的费用占私人健康支出中的将近80%,而与此同时,1990-2000年间,医药费用增加了8-10倍。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健康支出仍然处在非常低的水平。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1000-2200美元之间)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2200-7000美元之间)的平均比例为2.25%,而中国只有0.62%(参见表2)。 表2 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各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单位:%;年份:1997-1998) 政府总支出 健康 教育 国防 利息支出 中国(中央政府) 18.89 0.62 1.86 1.14 n.a 巴西 31.82 1.83 1.09 0.98 3.42 阿尔巴尼亚 29.01 1.14 0.64 1.13 6.64 罗马尼亚 19.87 2.23 3.06 2.09 2.62 菲律宾 19.26 0.56 3.96 1.36 3.47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28.83 2.25 4.05 2.31 3.31 资料来源:P.Musgrove and R.Zeramdini,2001: “A Summary Description of Health Financing in WHO Member States”, CM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WG3:3. 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1)由于中国缺乏应对传染病的基层卫生组织,将放大疫情爆发之后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据估计,10%的中国人口患有甲型肝炎,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只有1%。大约有500多万人患肺结核病,在世界上排名第二,而且其中许多病例具有抗药性。一些国外机构表示,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新生儿破伤风和乙肝患病率是亚洲最高的。全国防治艾滋病中心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人,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艾滋病人最多的国家。(2)疾病带来贫穷,也将加剧贫富分化。疾病摧毁了人们的身体,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能力或是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儿童可能为了挣钱给家庭成员看病,根本就得不到上学的机会;疾病或营养不良影响到儿童在学校学习的效率,也影响到成年劳动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兴趣;沉重的医疗费用减少了家庭的储蓄,影响到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终又减少了家庭的人均收入。这种贫穷-疾病的恶性循环毁掉了很多家庭对生活的希望。城市和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体制下存在巨大鸿沟,偏远的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而那里的7个省和自治区只获得了5%的医疗保健经费,1/4左右的医疗保健经费向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富裕地区倾斜。(3)目前中国人口的总负担系数(被抚养人口即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只有40%,远远低于亚洲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7%,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按照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中国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速度会更为迅猛,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里昂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将在未来20年左右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其理由是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过了这20年呢?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够在40年内维持高于7%的平均增长速度的国家也只有韩国和新加坡,如果放宽到5%,也至多增加日本、土耳其等国家,可谓寥寥无几。所以未来20年是中国经济跳跃龙门的最后一次尝试。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至关重要,颇有点像《生死时速》中的那辆公共汽车,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会引发爆炸。如果不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未来20年内想办法拆除隐藏的炸弹,到车速降下来,必定大难将至。 良政改革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成功处理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只有当一个政府拥有了良好的治理结构之后,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良政”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200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提出,良好的政府治理包括:(1)公民的发言权和政府的可监督性(accountability),即政府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公民能够通过有效和及时的信息对政府的决策进行监督;(2)政治稳定,即政府消除暴力、犯罪和恐怖活动的能力;(3)政府效率,即政府决策的质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4)减少不必要的管制,消除对企业和公民的制度负担;(5)法律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司法独立性等)(6)控制腐败。 我们认为,SARS危机为中国的良政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SARS危机是一场公共卫生体系的危机,按照传统的看法,这个问题属于“低政治”(low politics),但实际上在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如各级政府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对信息不予披露反而隐瞒真相、官员目标函数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而对民生重视不够等。借用熊彼特的话,危机也是“创造性的毁灭”。危机可以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并渲染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越高,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越高。当迷雾笼罩了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领导人站出来,而且我们需要他们就站在我们身旁。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决心,我们还等待看到他们的远见。他们要告诉我们,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 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结构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机之后,痛定思痛,政府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并推广危机应对机制。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时候,首先需要出动的是一支精干、高效、灵活的危机处理小组,但是目前调度的仍然是整个官僚体系,仍然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和政治动员。这好比逢山开道需要一把锋利的斧子,但是手边却只有一把沉重的榔头。吸取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建立专门的危机应对机制。 (2)政府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政府应该保持对媒体的影响力,以便赢得媒体和公共舆论对政府的支持。在信息提供渠道日益多元化、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对媒体的垄断和直接控制反而无法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因为媒体受到政府控制和媒体发布真实信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为了提高公众对政府的可信度、政府在公众中的亲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对媒体的影响转入幕后,而政府的公共关系体制走向前台。 (3)公共财政支持改革公共卫生体制。从公共卫生体制的历史演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卫生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而政府之所以愿意介入公共卫生体制,一方面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出现提高了公众对公共健康的需求,政府为了提高其合法性,必须不断增加对公共健康的供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共健康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提高了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对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国家对全国人口状况有详尽的了解,这也是国家提高统治效率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传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对全国人口注射疫苗、发动公共卫生运动、在紧急情况下对民间资源的征用、隔离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甚至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戒烟、戒酒)等都在无形中显示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首先必须在公共产品的框架秩序,对公共卫生的各项内容仔细进行厘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政府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民间部门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民间部分提供,但是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植的;哪些需要加强政府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放松政府干预的。 (4)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SARS还反映出来,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力量已经不够,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公民和企业的参与和发言权对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效率至关重要。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制度无法有效保证政府的决策质量。在“博弈模式”下,政府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由公民的参与最终“背书”。首先,应该向有用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时、畅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提供有关政府决策、预算、统计资料、财务披露等信息。其次,应该将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制度化。淡化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政策色彩”,如通过吸收民营企业家从政来显示政府对发展民营企业的决心。尽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进入决策过程,创造一个利益集团充分竞争的政治环境。如果利益集团之间能够形成充分竞争且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占据明显的优势,对于政府来说将是最优的选择。政府不用担心成为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俘虏”政府,同时又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支持。 (5)调整政府施政目标。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国从“增长优先”的目标,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将逐渐从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转变到真正关心民生问题。 公众对于政府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在目前的情况下,公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在官方的报道中,我们能够读到的只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SARS”云云的话。这些话除了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性”,实在是不能代表真实的公共舆论,倒不如说它们反映出了公众对政府不切实际的期待。 是的,只要不到最坏的结局,我们可以“对付”过这场危机。但是,这绝不是说政治可以高于灾害和风险。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天意难测,灾难的降临是命中注定,所以他们并没有那种政府能够逢凶化吉、救灾救难的期望。到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按照韦伯的说法,政府就是要“祛魔”,政府是人类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化身。既然人们相信理性和科学能够战胜自然,政府自然应该承担消灭风险的责任。正如真理再向前行一步就是谬误,对政府的过高期望使得公众形成了一个“无限关心的政府”(caring government)的想像。人们认为,首先,政府理应有办法防止风险和灾难的发生,如果风险和灾难发生,那么一定是政府的决策失误,其次,当灾难发生之后,政府有责任承担所有的损失。这种“无限关心的政府”的期望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还有误导性:政府的决策失误对危机的到来可能并不负有主要责任,比如在东亚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马上转而责怪这些国家的政策失误,但实际上东亚国家宏观基本面的情况一直表现不错;政府也不可能承担所有的损失。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责任只能对政府信誉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且一旦定下来由政府承担所有损失的规矩,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大家会变得对风险更加麻木,对政府更加依赖。 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心态。面对SARS,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何帆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