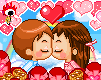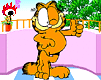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近20年来,中国的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公共健康状况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提高。1980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每千人)为42,到2000年已经降低到32。198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到2000年已经增加到70岁。但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其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系统做了调查,并根据健康改善、政府责任、医疗提供的公平性等做了排名,中国的排名为第144位,排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孟加拉国的后面。
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
(1)由于中国缺乏应对传染病的基层卫生组织,将放大疫情爆发之后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据估计,10%的中国人口患有甲型肝炎,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只有1%。大约有500多万人患肺结核病,在世界上排名第二,而且其中许多病例具有抗药性。一些国外机构表示,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新生儿破伤风和乙肝患病率是亚洲最高的。全国防治艾滋病中心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人,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艾滋病人最多的国家。
(2)疾病带来贫穷,也将加剧贫富分化。疾病摧毁了人们的身体,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能力或是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儿童可能为了挣钱给家庭成员看病,根本就得不到上学的机会;疾病或营养不良影响到儿童在学校学习的效率,也影响到成年劳动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兴趣;沉重的医疗费用减少了家庭的储蓄,影响到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终又减少了家庭的人均收入。这种贫穷-疾病的恶性循环毁掉了很多家庭对生活的希望。城市和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体制下存在巨大鸿沟。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能够分到的公共卫生资源(如政府卫生支出、医院床位数和护士数等)却不到40%。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97),1993年中国城市人均卫生支出(公共和私人)是乡村人均支出的4倍。大约7亿农民必须自己为所有医疗服务付费。毛泽东同志当年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偏远的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而那里的7个省和自治区只获得了5%的医疗保健经费,1/4左右的医疗保健经费向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富裕地区倾斜。1998年北京和上海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分别为6.10张和5.23张,贵州为1.54张,北京和上海每千人口医生数分别为4.72人和3.85人,贵州为1.25人;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和99.8%,但是西藏只有11.9%,甘肃为28.9%,安徽、江西、四川、贵州、宁夏均在40%以下。卫生部对全国农村114个贫困县卫生保健调查显示,贫困地区重点妇女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3-5.4倍之间,儿童健康检查率只有14.4%,四苗计划免疫覆盖率在26-99%之间,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目前中国人口的总负担系数(被抚养人口即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只有40%,远远低于亚洲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7%,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按照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中国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速度会更为迅猛,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仅仅依靠闪闪发亮的CDP增长数字已经不再能增加人民的幸福感,政府惟有更加发自内心地关注民生,才能切实提高其合法性,其中的一个当务之急是重建公共卫生体系。
什么是公共卫生?不妨引用Winslow早在1920年的堪称经典的定义:“公共卫生是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改善身体健康和机能的科学和实践。公共卫生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控制地区性的疾病、教育人们关于个人卫生的知识、组织医护力量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预防治疗,并建立一套社会体制,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享有能够维持身体健康的生活水准。”人们对公共卫生的理解不断变化、日益深入,但是,就从Winslow80多年前的这个定义,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公共卫生的实质是公共政策。
说到公共政策,需要进一步补充两点:(1)公共政策的主角一定是国家。只有当国家介入之后,像卫生这样的潜在的政策领域才能够由暗至明,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只有当一种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之后,各个阶层围绕该政策的博弈才能够遵循一种更清晰的游戏规则,人们也更容易看出来围绕某项政策的各方的不同观点和真正立场。(2)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国家是社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政策决策的最终结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不单单取决于国家,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各个阶层对政策的反应。
公共卫生体制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首先在于通过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由于能够用于公共卫生的资源是有限的,政府不能不切实际地试图为每个人提供所有的服务,而是应该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是农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穷人无力承受绝大多数医疗服务的费用,甚至无力为此借钱。为穷人的健康投资,既提高了穷人的生产率和教育程度,又有利于消除贫困和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这正是公平和效率可以兼得的政策。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是针对家庭和社区中的公共卫生和基本的临床服务。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的报告《为健康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考虑为公共卫生投资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增加用于基本公共医疗卫生计划的开支,其中包括免疫、传染病防治、基本临床服务(如患儿护理、计划生育、围产期护理以及肺结核及性传播疾病的治疗等)。现代化的医院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固然显得很气派,但是其机会成本则是贫困人口因为缺少足够的财政支持而陷入疾病和贫穷的恶性循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只覆盖了总人口的15%,但是却占用了2/3的公共卫生支出,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其成为了既没有效率,又显然失去公平的政策。
过去,政府一直是直接办医院、管医院,这导致了卫生部更多地是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代言人,为了让政府和卫生部真正成为12亿人民和患者的利益代言人,应该转变在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生产者主权观念”,政府不应该再一味地保护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应该是“需求导向”,即保护消费者的主权,尊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支持不仅仅是投入更多的钱,还包括市场准入、卫生监督、立法执法、提供信息和教育等。必须在公共产品的框架秩序,对公共卫生的各项内容仔细进行厘定。有些卫生服务是需要政府出资、政府承办的,比如接种疫苗和防治SARS;有些卫生服务是可以由政府出资、民间部门承办的,比如对贫困人口提供医疗券,而由患者自己选择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有些卫生服务是可以由民间部分提供,但需要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植的,比如社区医疗、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在某些领域,政府需要加强管制,比如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管理;在有些领域,政府却需要放松管制,比如鼓励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允许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医药销售行业、开办医院等。
地方政府的参与是公共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关键。这其中可能会有种种矛盾,比如地方政府可能会把公共卫生视为中央对地方自主权的限制,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改革反而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设计公共卫生改革政策的时候,如果没有妥善地为地方政府想好如何解决资金和人力的来源,富有理想主义的美好改革方案往往会在执行的过程中走样,要么流于形式,甚至与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公共卫生的积极性,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应逐渐从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的数量等指标转变为真正关心民生问题。这需要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如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最低标准,或是建立衡量公共卫生绩效的一套指标体系;(2)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公共财政主要支持较落后的地区,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在公共卫生改革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由于公共卫生实际上是投资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改善也容易增加民众的认同,因此通过适当的激励,是可以鼓励一些地方在建立公共卫生体制方面发挥表率作用的;(3)SARS危机暴露了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严重问题,比如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头更猛,各地区之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战,应该得到足够的警惕的重视。
SARS危机中,一个颇具讽刺的现象是,一边是轰轰烈烈的全民动员,另一边则是寂静无声的社会团体和NGO。政治运动式的全民动员恰恰衬托出来政府在面对危机时的孤独无助。在传统体制下,单位制(如居委会)在城市里几乎覆盖了全体居民,在有灾害或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只要动员单位,反应很快、很有效。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人口的流动和信息的传播,危机和灾难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信心打击可以较容易地被限制在一个地区之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的职能已经大大弱化,越来越多的群体游离于单位之外,比如在外企和私人企业上班的员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等等。政府几乎完全承受了抵抗SARS的压力,国内的民间组织没有发育,无法发挥作用;由于缺乏散财以济天下的传统和机制,富人和企业在SARS危机中表现得格外安静;从国外的经验看,在灾难事件和疫情之后,总是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大显身手的时候,但是宗教团体的身影根本没有出现。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天意难测,灾难的降临是命中注定,所以他们并没有那种政府能够逢凶化吉、救灾救难的期望。到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按照韦伯的说法,政府就是要“祛魔”,政府是人类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化身。既然人们相信理性和科学能够战胜自然,政府自然应该承担消灭风险的责任。正如真理再向前行一步就是谬误,对政府的过高期望使得公众形成了一个“无限关心的政府”(caring government)的想像。SARS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政府在应对风险的时候,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在政府的能力难以达到的领域,需要社会各种民间力量的支持。在一个风险层出不穷的现代社会,永远不要试图让政治高于灾害和风险。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