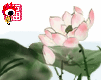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和李约瑟之迷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22日 18:23 中评网 | |||||||||
|
姚洋 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刚在内战中取胜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带领八万士兵,在现今秘鲁的高地小镇卡加马卡(Cajamaca)迎战由文盲佛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的168名西班牙入侵者。然而,这场看似力量对比悬殊的战役的结果,却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当望见印加人华丽的宿营帐篷和浩大的军队的时候,就连西班牙人自己也觉得是自投罗网。但是
很显然,决定这场战役的关键因素是西班牙人手中的长枪和钢刀,而此次战役也不是西班牙征服者以少胜多的唯一一场战役,类似的战役还发生过几次。这些战役对于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没有消灭印加帝国的人口。真正使南、北美洲几千万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的因素,是欧洲人所带来的细菌和病毒。例如,麻疹于1520年由一个西班牙人的奴隶带入墨西哥,在以后的一百年间,墨西哥境内的印第安人由大约2千万锐减到160万。病菌的杀伤力远远大于刀枪的杀伤力。 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首先使用刀枪呢?为什么是欧洲人把病菌传染给了印第安人、而不是反过来呢?这是杰瑞德·戴尔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诸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戴尔蒙德的问题比上述问题更宽泛,他试图解释人类文明的地域差异:为什么人类文明起源于欧亚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至今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而欧亚大陆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戴尔蒙德对此的回答既传统又新颖:所有这些差异都来自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此说如何新颖,留待后面再说;它之所以传统,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十九世纪就产生了。记得八十年代初刚上北大地理系的时候,胡兆量教授在《经济地理概论》中首先讲到的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从此之后,凡是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的言论,我都避而远之,甚至持批判态度。在经济学界,有一些人非常强调地理环境对一国一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如,原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对中国各省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现进行了数量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省会城市离运河越近的省,其经济表现越好。可是,运河是人所修造的,因此会不会有意往经济发达的地区修呢?如此这样的问题,让我对地理环境的解释力持怀疑态度。因此,当我看到戴尔蒙德又提地理环境时,心中不免生疑,同时也心生好奇,开始读这部洋洋四百多页的厚书。没想到,此书的语言和叙事像磁力一般把我吸引住了,让我在短短一周内读完了全书。戴尔蒙德在书中并没有提供新的史实,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以新的视角把人类过去1万年的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他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此书获得了普利策奖。 戴尔蒙德的本行是生物学,他对人类社会的兴趣起源于他在新几内亚的长期的田野工作。在和当地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他发现,当地的许多人其实非常聪明,而新几内亚人口的整体智力水平绝不低于欧洲人。但是,正如一位当地政治领袖亚力在三十年前问戴尔蒙德的:“为什么我们就是不如你们白人?”正是为了解答亚力的问题,戴尔蒙德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而言,历史只从人类建立了社会组织开始;而戴尔蒙德的自然科学背景引领他把历史的起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去研究人类脱离自然界的过程。 人类脱离自然界的起点是定居农业的产生。在此之前,人类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在本质上和动物无异。定居农业为人类提供了可以储存的剩余,使得一些人可以从生产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文化、艺术、管理和宗教等事务。与此同时,剩余的产生还导致了对制度的需求。一方面,人类需要一套所有权制度来界定剩余的归属;另一方面,人类还需要一个公共机构来实施对所有权的保护。同时,定居生活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因此也产生了对国家结构的需求。因此,定居农业是人类诸社会走向分岔的起点。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上有五个无可争议的农业起源中心:美索不达美亚平原、中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美洲地区、南美安第斯地区和美国东部地区。但是,位于欧亚大陆的美索不达美亚和中国所驯化的植物远较其它地区多,并且,这两个地区的作物的营养价值更高。比如,美索不达美亚驯化了小麦,中国驯化了水稻和小米。与此同时,这两个地区也驯化了更多的今天仍然在饲养的大型家畜:美索不达美亚驯化了绵羊和山羊,中国驯化了猪,而其它地区要么没有驯化任何家畜,要么只驯化了小型动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呢?戴尔蒙德认为,这是因为美索不达美亚和中国拥有更多的适合于驯化的野生作物和动物。非洲的动、植物资源也非常丰富,但适合于驯化的却不多。比如,斑马是非洲非常普遍的动物,但它的性情暴躁,经常咬人致伤;因此,尽管人们也尝试驯化斑马,但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另外,可驯化的动物还必须以草为主食、生长期较短、且体型较大,以便人类在较短的时间内以低廉的饲料换取他们的肉。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具有绝对的优势,它拥有72种符合条件的野生动物,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51种,美洲只有24种,澳洲仅有1种。在迄今为止人类饲养的14种家畜中,欧亚大陆就驯化了13种。 欧亚大陆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的原始驯化,而且有利于动植物的传播。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发育过程中,传播比原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欧亚大陆的传播优势来源于它的东西向的地理主轴,地球的气候一般是以纬度来区分的,同纬度的地区基本属于同一种气候。欧亚大陆的东西向地理主轴因此使得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变得较为容易。相反,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地理主轴是南北向的,它们的气候在南北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阻碍了驯化动、植物的传播。比如,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美亚发源的作物,到了公元前3800年就传播到了北欧和英国;相反,在南、北美洲分别驯化的作物和动物,要经过500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对方同样的气候地区,因为两者之间的热带地区阻断了动、植物的传播。 然而,定居农业的后果并不总是好的,一个随定居农业而产生的重大问题是病菌的传播。对人类具有杀伤力的病菌都来源于动物,因此,驯化动物较多、人口密度较大的欧亚大陆成为病菌的发祥地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传播了疾病,而不是印第安人向欧洲人传播了疾病。 解决了农业和病菌的起源问题,这以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农业发达的地区首先产生了文字,随后向周边地区扩散;同时,技术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人们学会制造刀枪等杀人武器;最后,社会组织也变得日益复杂,君主制度等集权体制代替了较为平等的部族首领制。这些文明的分岔现象因此可以看作是定居农业的副产品,进而又是各文明所处地理环境的产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戴尔蒙德对待地理环境的态度和十九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后者那里,地理环境起作用,是因为它改变人的性格:生活在温带的人更勤劳,而生活在热带的人更懒惰。戴尔蒙德所反对的,正是这种种族主义的观点。他的书的起点是,人类社会不分种族,生来具备同样的平均智力水平。人类诸社会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巨大的差别,是因为各个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限制或鼓励了它们的发展。戴尔蒙德将人类社会分岔的起点上溯至农业的起源,在那个起点上,人类无疑受到地理环境的巨大约束,由此而产生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戴尔蒙德没有解释的,是各大洲内部的差异。定居农业是人类诸社会分岔的起点,在此之后,分岔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加剧。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解释这些导致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的文明分岔也许更为重要。这其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李约瑟之迷:中国在古代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但到近代为什么却落后了呢?近代世界的分水岭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因此,李约瑟之迷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关于这个谜,有许多解释。戴尔蒙德的书主要讨论人类社会脱离自然界时的分岔,但在书的结尾处,他也给出了对李约瑟之迷的一个解释。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地理环境。如果我们随意地查看一下欧洲和中国的海岸线,马上就会发现,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前者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后者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戴尔蒙德以航海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生于意大利,为了他的伟大的航海计划,先后投靠了三、四位欧洲君主,最后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支持。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了哥伦布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了。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宦官一旦失势,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因此,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统一的国家体制。 但是,这个解释虽然对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与戴尔蒙德的解释相类似的是中央集权的税收假说。1998年夏天,我到美国巴尔的摩市参加留美经济学会的夏季年会,同室的是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生。这位美国仁兄高高大大,研究的却是中国经济史。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南宋时期的税收制度的,其基本观点是,在南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工厂化工业的萌芽,但却被高度集权的中央税收所扼杀了。南宋时期,江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外患频仍的南宋王朝为了战争而大肆向工商业课税,而且,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税收留成。由此一来,地方官员无心扶持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相反却加强税收力度,以向朝廷交差了事,工商业因此在重赋之下凋敝了。2001年夏天,我到厦门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召开的年会,恰巧又与这位老兄同住一室。原来,他已经在台北中研院下属的经济所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并刚刚娶了一位台湾太太;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进展,真是双喜临门。他告诉我,为了更好地理解宋代财政,他不得不了解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为此,他已经回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了。虽然我们用英语交谈,但我相信,他的古文阅读能力肯定大大地超过了我的。几年的研究更坚定了他当初的看法,即南宋时期高度集权的税收体制是打开李约瑟之迷的钥匙。 然而,这个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中央,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帝就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更一般化的解释来自于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比如,明末清官海瑞的断案方针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是封建官吏的典范,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黄仁宇认为,这种思想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仁宇从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一方面,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以德治代替法治所造成的后果有深刻的洞察(读一下他的《万历十五年》,感受一下万历皇帝在群臣的道德围攻下的无能为力,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对诺斯的理论的引用也贴切到位。但是,问题在于,所有权的建立是否真如诺斯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起飞(更确切地说,是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吗?如果真是这样,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理论,乃至大部分经济学都可以废弃了,而这些领域的发展恰恰说明,所有权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因此,要解开李约瑟之迷,我们还需要新的理论。 尹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在于197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式样》一书中,尹懋可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尹懋可列举了许多史实,试图证明中国在明末和清朝已经遭遇到了资源约束的瓶颈,从而无法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尹懋可关于中国农业的论述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但他关于中国工业的解释却缺乏说服力,甚至有逻辑错误。所谓的资源约束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资源约束。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在明清时期就遭遇了无法克服的资源约束瓶颈,则我们今天就可以躺倒睡觉了,因为任何努力都不会有回报。尹懋可大概也认为资源约束是相对的,中国在明清时期的资源瓶颈是相对于当时的技术而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尹懋可想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新的工业技术,却又把新技术当作缓解资源约束的前提条件了。 但是,只要稍做经济学的修改,尹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说仍然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工业。我们可以回到中国人多地少的事实,考察由此而带来的工农业回报的差距。直到现代时期,中国的农业资本回报一直高于工业的资本回报,这可以从南方大量存在的不在村地主现象得到证明。这些地主因为在城镇拥有工商业才离开农村(或者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镇),但又无一例外地在乡下购置土地。如果这样的人只是少数,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脱掉土财主的习气;但是,大量不在村地主的存在就不能简单地以个人偏好来解释了,而只能是因为农业的资本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资本平均回报的缘故。据葛剑雄在《中国人口简史》中的估计,在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口一直在6千万到1亿之间徘徊;但是,经过清代的“人口奇迹”,中国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达到4.5亿。可想而知,在相对狭小的可耕地上要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土地的价值必然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相反,欧洲由于人口密度低,较低的农业水平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工业回报因此高于农业回报,资金向工业集中,欧洲因此向一个高水平的均衡发展。 因此,经过修改之后,尹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可以解释西欧和中国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而且,这是一个基于地理环境的经济学理论。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些细节。依我看来,尹懋可的理论有赖于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人口的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即当人均收入超过长期均衡工资时人口有的正的增长,相反,人口出现负增长;另一个是工业具有规模经济。第一个假设保证农业技术提高所带来的剩余被人口的增长所吞没;在十九世纪及以前,这个假设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第二个假设也具有现实性,因为任何工业生产都涉及一定的起始成本,而起始成本带来规模经济(比如,电信业就是这样)。如果工业中不存在规模经济,则即使工业品的价格较低也会有人去生产,因为赢利总是可能的。这显然会破坏尹懋可的理论。反过来,如果工业具有规模经济,则只有当规模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投资工业才会开始赢利(如电信业,只有客户群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会赢利)。此时,尹懋可的理论预测才会成立。 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在经济学范畴内提出来的。在此之外,还存在其它一些非经济学的解释。第一个这种解释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大小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教授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来完成,所以,中国较大的人口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但是,现代技术不是建立在经验、而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人多因此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技术创新。但是,这个解释所忽视的,是工业革命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的,如同诺斯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公认的时期为1750年-1850年)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公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早了近百年。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身处其高潮的亚当·斯密没有注意到它,而与他同时代的马尔萨斯更是对人类前景持悲观态度。工业革命中的许多技术是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熟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事实是,瓦特只是在前人的发明上做了重大的改进,以使得它更为实用。蒸汽机的雏形是英国人托马斯·萨瓦瑞(Thomas Savery)于1688年发明的,真正实用的蒸汽机是由另一个英国人托马斯·纽可曼(Thomas Newcomen)在1705年发明的。但是,这种蒸汽机极其浪费能源,因为它不使用压缩空气。直到1768年,瓦特才发明了更加实用的蒸汽机,但人类还要等到15年之后,才能看到它被用来驱动车轮。 李约瑟本人也给出他自己所提出的谜语的解答。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这种说法有多大合理性,还有待于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去评判,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即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和欧洲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并没有依赖于科学的帮助。 也有人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特别是科举制度来寻找李约瑟之迷的答案。科举制度不仅扼杀了青年人的创造性,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诱使人们都去争过科举的独木桥,唯读书、做官是尊,而轻视发明创造和商业活动。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宽泛,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些具体的东西。同时,一个好的激励结构也未必是产生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如果尹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说成立的话,一个好的激励结构也就只能激励更多的农业创新,工业革命照样不能发生。 看来,以上关于李约瑟之迷的任何解答都不可能单独解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最近,有人向我推荐一本新书《国富国穷:为什么一些国家如此之富,而另一些国家如此之穷》,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新的观点。于是,我趁在日本讲课之际,从亚马逊书店邮购了这本书。谁知,读后大失所望,作者戴维·兰德斯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至少对于我们解释中国的衰落是如此。诚实地讲,岂只是大失所望,我甚至产生了愤怒。这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史教授是一个大胆的、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者(也许,这本书之所以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也是因为作者道出了美国右翼势力一直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理话?),不仅堂而皇之地鼓吹欧洲特殊论,而且对其它地区极尽其蔑视之能事。他虽然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却对中国历史要么不甚了解,要么带着深度的有色眼镜去了解。 比如,他认为欧洲人在中世纪发明了钟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顺便提一句,兰德斯认为中世纪欧洲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和进步,因此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中国人把时间看作是皇权的特权,“在城市,鼓和其它噪声发生器(noise makers)被用来报时;而且,皇室的日历在所有地方规定了季节和其中的活动。日历也不是统一和确定的,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日历,将他们的封印刻在时间之河上。私人对日历的计算因此变得毫无意义。”(第50页,着重号为笔者后加)这种无知和傲慢竟会出自一个身处现代的大学教授,让人吃惊。不仅如此,兰德斯对中国的蔑视更是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认为中国人口多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大家庭(这种观点已经被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所否定),人多“消耗更多的食物,而食物又导致更多的人。Treadmill.”这最后的一个单词,我是查了字典之后才确定了它的意思的,意为“人力脱粒机”,或“单调而讨厌的、周而复始的动作”,不管是哪种意思,都是侮辱性的。兰德斯教授这种无知的勇猛和傲慢,让我联想起一种动物,那就是……森林里跑出来的野猪。你可以把这种动物的所有品行特征和兰德斯教授联系起来。 作者都是美国人,但《枪炮、病菌和钢铁》和《国富国穷》两本书给人的感觉完全相反,一个开放、生动,另一个傲慢、狭隘;说到底,是因为两位作者所代表的观念和势力不同。戴尔蒙德反对种族主义,而兰德斯则宣扬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种族主义。关于这一点,读者在读了这两本书之后自然会有所体会。至于李约瑟之迷的答案,还需要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正当我们跨入纪元之后的第三个千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显示出了重新崛起的趋势,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汤比因的文明周期理论。也许,相对于文明的周期波动,前面所介绍的所有理论都不过是对文明的短期扰动的解释?也许,在中国文明于唐代达到顶峰之后,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它滑入明清时期的低谷?迄今为止,我们只经历了一次历史长波,因此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做出一般性的回答。或许,只有等到下一个千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姚洋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