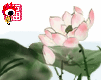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道德的两个层次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22日 18:22 中评网 | |||||||||
|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 姚洋 倡导人类的自利行为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达到人类整体最大福利的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的同时也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赞美人类的同情心和道德,
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基础,但这个问题斯密在二百年前就解决了:在他看来,这个规则基础就是正义。虽然斯密没有对正义下一个明显的定义,但从他的行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把自已放到他人的位置上,考察自己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并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即孔夫子所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者也。为什么要将自己放到他人的位置上去考察自己的行为呢?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不比另一个人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而且只有自己才能了解自己的感觉。在这里,斯密要求的是人与之间的对等性。但与他在《国富论》中对人性的假设相一致,这种对等性是建立在个人的自利基础上的:你用不着去相信他人的感觉,正义只是建立在把你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你自己认定你的行为合理的基础之上。当然,这种正义的一个前提是每个人都具备随时进行冷静思考的能力。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说那些总是被偏见所左右的人,即使是一般人,也难免有被情绪所支配的时候。但是,对于斯密的理性人来说,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让我们权且接受这个假设,继续对正义的讨论。 斯密没有说清楚、我们也无法说清楚,基于对等性的正义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但是,它排除了许多我们所认为不正义的事情,如偷盗、杀人、占他人便宜、限制他人自由等等。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正义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游戏规则,是市场达到其效率不可或缺的东西。斯密将正义和基于仁慈的道德进行了区分。斯密说:“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又说:“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第106页)。斯密之所以强调正义的重要地位,我以为,是因为正义是令自利行为在看不见的手控制下达到人类最大福祉所需要的最起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最起码的条件,人类的利已行为就会将人类带入霍布斯的野兽世界。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一个人的利已行为止于不对他人构成直接的伤害。“在追求名誉、财富和显赫地位的竞争中,为了超过一切对手,他可尽其所能地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挤掉或打倒对手,旁观者对他的迁就就会完全停止。”(第103页)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出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换一个角度看,正义允许人们对不是由自己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表示出漠不关心。我努力地工作,试图超出我的竞争对手,只要手段光明正大,符合正义的要求,竞争对手的破产则不应由我来负责,因为是市场,而不是我直接导致了他的破产。再者,我们也无须对与己无关的不义行为进行谴责或纠正。一个看到小偷而不去追赶的人可能是不道德的,却没有违反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义是一种被动的约束,它只要求人们保持对他人的尊重,但不要求人们去主动为他人的福祉尽力。由此可见,斯密的正义原则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在很大程度上,斯密的正义与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是重合的,因为两者均将人看作平等的个体,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规则,都不带感情色彩,而惩治不义行为又都是两者的责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牙还牙似乎是造物主指令我们实行的主要规则。”(第101页)但是,如果法律仅仅停留在为受害者伸冤这个层次上则远远不够。当我们要求对施害者进行惩罚时,“与其说是对那个受到伤害的人的关心,不如说是对社会总的利益的关心。”(第111页)这里体现的仍然是斯密的中心思想:正义是支撑人类社会的主要支柱,伸张正义理所当然地要以社会的整体福祉为目标。在这里,斯密更像一个功利主义者,而不像一个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以当代法律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和具有前瞻性的。传统法学以道德为基础,现代法律经济学则强调社会福利分析的重要性,而斯密的思想则是这种分析范式的开先河者。 当我们将正义和法律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的规则基础就是一国的法治。但是,法律制度是冷冰冰的,为的仅仅是人们可以在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无形空间里和睦相处。如果仅仅有正义和支撑它的法律,人类大概会过着一种类似机器人所过的生活。人类还需要同情。谁能毫不羞愧地宣称,他在一片反对声中从不期待一丁点儿赞同的表示?但是,正义的行为不需要同情。比如,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公共汽车的座位上看着一位孕妇站着,因为正义不要求我给她让位子:我的行为根本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同情心要求我感受她正在忍受的痛苦,也就是说,我必须接受她的感觉;这样一来,同情心就会驱使我让出自己的位子。正义允许我从自己的角度看别人,同情则要求我从别人的角度看别人。 再者,正义需要法律来表达,而法律从来就不可能是完备的。因此,在正义的名义下可能发生对社会不利的结果。辛普森案便是一个例子。在那里,正义完全被法律文本和程序所左右,而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即辛普森杀人这一事实,却被搁置在一边。 另一方面,只有正义,一个经济系统是否就可以达到最高效率呢?换言之,是否存在能够增加社会效率的补充机制呢?首先,只有正义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交易成本高昂的社会。比如,就囚徒困境而言,参与者可能需长时间的重复过程才能找到对群体来说最优的结果。如果存在道德约束,则群体进行的就是阿玛蒂亚·森所说的信任博弈 --- 一个每个人都信任每个其他人会采用一个有益于社会的策略的博弈,社会最优从一开始就可以达到,因此也就不会出现类似公共地悲剧的事情了。其次,只有正义而无道德的社会可能使得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让我们来看看合同的执行问题。哈特的一个贡献是发现了合同的不完备性是产生所有权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合同的不完备性所带来的重新谈判问题,且当对方资产与自己的资产互补时,厂家会将对方收购下来。也就是说,所有权是解决合同不完备性的手段。但是,所有权本身也是一种合同,一种个人通过国家与其他所有的人签订的合同,因此它本身就是不完备的。巴泽尔强调所有权中的公共领域,正是这个意思。一个企业主可以拥有他的企业的法律所有权,从而对他的雇员的工资和工作量有决定权。但是,雇员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如怠工、降低工作质量等等,来蚕食企业主的所有权。法律只能赋予企业主一个抽象的名义所有权,具体的所有权取决于企业主对维护其所有权的成本-效益分析。维护所有权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必须对雇员进行监督,而最优的监督很少会是完备的,因为监督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这正是所有权不可能完备的原因。于是,我们便有了“哈特悖论”:既然所有权本身是一个不完备的合同,它如何能解决其它合同的不完备性呢?答案在于,人们利用其它非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合同(包括所有权)的不完备性问题。 道德就是这些手段之一。在斯密那里,道德的实质是同情心,是一个人对他的同胞的爱和对自我利益的克制。他将道德描述为我们“心中的那个居民”的判断。他热情地呕歌,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第166页)道德是一种不受个人经济利益支配的命令。怠工可以获得个人利益,但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会受到“心中的那个居民”的谴责,因为怠工是不道德的。和正义相比,道德是主动的。它要求一个人对哪怕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的不幸表示同情;它要求一个人在看到不义的行为时挺身而出,对其进行谴责和制止;它要求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间接地影响到他人的福祉的时候克制自己;……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变得丰富多彩;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运转得有序、和谐;也正因为有了道德,我们的经济系统才在不知不觉中节省了大量的成本。道德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共同期望。有了它,我就可以肯定,当我行善的时候,别人会以同样的善心对待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善心都是发自我们“心中的那个居民”的命令。法律却无法给我这样的信心。虽然一个司机闯红灯是违法行为,但我无法肯定每个司机都会在遇到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因为在没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闯红灯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此,即使是绿灯亮时,我在过马路的时候也会小心慢行,以免被闯红灯的车撞倒。如果遵纪守法已经溶入了每个社会成员的血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的一部分,我大概会在过马路时大胆一些。道德的丧失正在使我们的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的企业家们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对付不道德者。货到付款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许多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按时付款,或干脆永远抵赖下去。由此一来,现金交易量大增,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一些企业怕上当受骗干脆少接单,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失去一些值得做的生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严格的执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述现象的发生频率,但法律是最昂贵的社会组织工具,如果每个人都具备道德,从而降低法律的使用频率,岂不是更好?道德虽然可能是景上添花,但是,缺了这朵花,我们的社会不知会颓败到什么程度! 道德的形成固然有自发的演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形成一种游戏规则,而不是包含着同情和自我克制的道德。出于社会个体的自发博弈从来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但在部分社会群体内所达到的博弈均衡却往往不能达到对全社会来说的最优结果。比如,在美国,职业道德可以看作一种自发形成的同一职业内部的人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律师这一行里,这个准则的基本要求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打赢一场官司。在辛普森一案中,科库伦为辛普森赢得官司的做法,以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来衡量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道德显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那种,因为我们所认定的道德要求我们对认定的不义行为采取负责的态度。 既然道德的要求超乎于人类利已之心之上、而又不可能是自发博弈的结果,道德的实施只能通过个人内心的强制。法律不能成为强制道德的手段,因为它不能逾越正义所允许的范畴,要求人们主动地对他人施于同情或为他人利益克制自己的较小利益。然而,要达到个人内心的强制,对于追求私利的个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过去,这种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惩罚达到的。一种惩罚是通过组织进行的。这些组织包括家庭、家族、教会等。但是,这种惩罚到了现代就变得不适宜了,对正义的要求迫使社会放弃这种惩罚。另一种惩罚是社会群体对违反道德的个人的指责乃至唾弃。当我们想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时,“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合宜对象。”(第166页)然而,群体压力只有当群体相对稳定时才能发挥作用,在社会流动性极大的今天,它的作用已经大大地弱化了。要想使道德成为“心中那个居民”的呼唤,必须内化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在这一点上,宗教大概是做得最好的。“在每一种宗教和世人见过的每一种迷信中,都有一个地狱和一个天堂,前者是为惩罚邪恶者而提供的地方,后者是为报答正义者而提供的地方。”(第113页)地狱和天堂都是未知世界里的东西,描述的是人死后的景象,因而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同时,对死亡的恐惧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这种恐惧和天堂、地狱的不可证伪性使得人们宁愿相信死后惩罚和报答的真实性。同时,宗教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强化行善的崇高感和作恶的罪恶感。比如,基督教创立了原罪说,以证明人生来就是为了赎罪,同时使得再次作恶变得逾加得不可饶恕。另一方面,基督教通过讲道与讲道场所的设计传递一种崇高感,从而使信教者从行善的行为中得到一种自我奖偿。对信教者个体来说,宗教首先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替代不可知世界的精神乐园;对社会来说,宗教则首先是一种足以内化道德惩罚的社会组织。 有人会说,教育可以起到与宗教相同的作用。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首先,要想使人们相信教育对道德的推崇,首先必须建立一套自恰和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论证道德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道德的命令性质,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理论是不可能的。道德好比数学里的公理,永远无法在同一个系统中得到证明。其次,教育没有一个可以伴随一个人终生的组织来支撑,因而其功能远不如宗教那样强大。我在这里将宗教和教育进行对比,是想说明组织在传输和实施道德方面的重要性。现代社会不再容忍通过组织的强制,但是,组织、还有与其相一致的仪式,可以造就一种道德氛围,内化人们的道德惩罚。 回到对“斯密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斯密看来,正义本身足以支撑人类社会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需要道德。但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如同一篇符合语法却毫无生气的文章,枯燥乏味;同时,一个没有道德的经济系统如同一架没有润滑过的机器,费时费力。斯密虽然没有意识到道德对市场经济的运作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追求促使他写下《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这与他对看不见的手掌握之下的利已之心的肯定毫不矛盾:虽然利己之心能将人类社会送上财富的顶峰,提倡道德,为人类社会景上添花又有何妨?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初稿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二稿 二000年九月十三日三稿 二00一年四月九日四稿 二00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五稿 《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胡企林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北京。 * 原文发表于以《道德情操》的篇名发表于《读书》2001年第10期。收录进本书时略有改动。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姚洋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