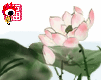| 国家与三农问题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22日 18:16 中评网 | |||||||||
|
姚洋
国家在处理三农问题的时候,要考虑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提高农民收入当然应该是国家政策的目标之一,但是,拔苗助长似地提高农民收入,其后果可能是灾难
这里涉及到国家的角色问题。因此,在讲三农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国家问题。我想做的,是区分积极的国家和消极的国家。消极的国家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最小国家,这是像哈耶克和诺齐克那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同的理想国家。在最小国家里,国家的唯一责任是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律之下,人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不多也不少。比如,比尔·盖茨并不比非洲的饥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失业和破产的人应该自己负责,国家没有责任。这种最小国家是不是可能的呢? 如果人是单面的、完全理性的,那么最小国家是可能的。这里,我解释一下理性人,理性人就是做了一件事不会后悔,用经济学的词语来说,就是要符合序贯理性。理性人不会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如果是这样,最小国家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国家不用为他们担心。但是,如果人是多面的,那他就会考虑多个方面,除了收入,他还要考虑地位、自我价值等等。事实上,每个文化都包含对公平的追求。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每种道德理论体系中都包括平等的内容,只是各自强调的方面不同。大多数人容易只强调一面,比如权利,而忽略其他方面。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看待平等。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不是人们常说的“红眼病”,而是一种对公平的基本认识。西方基督教里也有基本的平等的思想。此时,最小国家就不成立了。 历史也告诉我们,最小国家也是不存在的。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变》里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垄断资本家有意设计的,因为自由竞争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时,自由竞争被限制在他们自己内部,对于外部竞争,他们极力反对。比如英国的自由贸易,它只是对自己、对本国自由;对其他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相反,对工人的保护却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自发形成的。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对缓解美国的经济大危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罗斯福却建立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不断完善,对美国平稳地度过后来的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不存在最小国家。 另一种消极的国家是被挟持的国家。被挟持的国家就是指被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国家。比如,东欧的激进改革为什么失败呢?哈佛大学教授施莱佛做了很多研究,他认为东欧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政治势力将经济改革搞坏了。一个国家,不管是转型期的国家还是民主程度发达如美国的国家,如果成为了利益集团的工具,那么经济势必要受到破坏。比如印度,它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受利益集团左右的国家。我有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有一次应邀到印度访问,介绍中国改革的经验。印度同行要少讲经济改革的经验,而讲一讲中国反腐败的经验(笑)。中国可以处决一个副委员长的官员,印度实际上该处决的人很多,但是无法做到。印度的政党分左派和右派。右派执政时想对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左派就带领工人游行,使得右派的改革无法进行。但是当左派上台后,它也想私有化,因为国有企业的亏空太大了。此时,右派也去发动工人游行,阻止改革。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不管谁在台上,改革都无法进行。国家被政党政治所左右,就不能达到社会目标。 第三种消极的国家是商业化的国家。中国就有这样的倾向。它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相同,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来讲一下中国的财政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单一的共和国,地方服从中央,地方性法令、法规也必须处在中央的法令、法规之下。由于执政党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央在政治上对地方严格控制。但是在财政上,自从1958年放权之后就一直没有收上来,财政制度显示出强烈的联邦化倾向。而且,这种联邦化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邦化。像美国的联邦制,它在一个州之内的财政还是统一的。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每个县、每个区的财政都是独立的,最典型的,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些都统一不起来。对待企业也是这样,每级政府都不想要亏损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将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拿在手里,其他的下放到各省;到了省一级也是如此,将一向效益好的企业拿在手里,其他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企业就下放;各个城市也仿而效之。有一次,我们进行改制调查时发现,统计年鉴登记着的企业数远大于各市拥有的企业数。原来都在一年期间下放给区县了。到了区县一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放工人回家,工人失业,没有饭吃,这样就容易激化矛盾。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政治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而财政上相互独立,这就会使政府产生商业性行为。地方政府都变得非常理性。有一次,一个城市经贸委的领导对我说:“我们比学者都开放,有一次把一位教授都驳倒了。这个教授认为像水电煤气这样的公用事业是不能让私人经营的。我说,怎么不可以?香港不是把公交线路都拍卖了吗?” 在企业改制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是重庆。它是这样做的。企业改制时,先把工人划出来;然后清算资产,挑选一些职工留在企业,剩下的由政府来负担,从此,企业和政府就一刀两断了,各自的权责明确。重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对社会有利。遗憾的是,很少有地方能做到这样。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做的:你要想买我的企业,行!但必须全部接受我们企业的工人。这样一来,政府的危机就解除了,工人开不了支就会直接找经理,而不到政府来“上班”了,(工人上访、静坐叫“上班”)。企业是私人的了,有问题要找法院去解决。这是一个转移矛盾的做法。但是购买企业的人也不能平白无故增加这么多负担,他们就会跟政府谈判,要求资产打折,就是要以比企业的实际价格低得多的价格来买企业。各地都有资产打折的公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按照这个公式来做。这就要看企业经理跟市领导的关系了。根据了解,有的地方卖出土地的价格只有工业用地价格的五分之一!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造成人员和资产一锅粥的局面。企业到了新的经营者手中时,如果想进行新的资产组合就可能出现问题。有一家澳洲的公司买了一家天津的企业,当时低价买进,接受了全部工人。一段时间后,公司发现这个行业没前途,便把企业转手卖给另一个企业。它不管人,只卖资产;新的公司接手企业,自然要大裁员。工人要求公司承诺就业,但新公司说:“我买的是企业的资产,又不是连工人一块买的!”澳洲公司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合同上没有规定卖企业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安排工人。新的企业更没问题,买的是企业的资产而不是工人。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政府不承担责任,而是全部推给了企业。政府的行为是理性的。老板不给工人钱,工人自然会去找老板,而不是找政府;解决不了的话,就把老板告上法院,而跟政府无关。这在理性上是很清楚的。政府变成了商业性单位。但是对政府有利的行为不一定对社会有利。政府的商业性行为造成国家性机会主义,长期下去,政府的合法性就成为问题。其它财政联邦化的国家有配套的体制,如地方选举,使得政府要对民众负责,而中国缺少了这一环,这就使政府的“理性”行为越发偏离社会利益。 那么什么是积极的国家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对什么是好的、公正的社会做出明确的判断。比如美国,我们可以说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干涉别国的内政,但是,民主、自由的确是美国人价值观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就像我们所说的霸权主义在美国国内也是得到支持的。仔细想一想,美国的有些做法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么说下去话题就扯远了,跑到国际关系上了。总之,一个政府,一个社会,要有关于公正的标准。老百姓不管你说你代表谁,而是要问:你代表了我什么?你给了我什么?社会的分化日益明显,没有谁可以代表所有各阶层的人,关键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从理论上讲,一个公平的社会,就是一个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社会,公平就是全体公民所认同的最小范围的伦理规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社会公平的标准,就会被变成消极的国家,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一味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利益集团,但潜在的利益集团仍然发挥着作用。对于一个以代表全体人民为宗旨的政府而言,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要照顾到,政府因此变成了一个“救火队”,哪个集团喊得凶,就赶紧跑去安抚,国家因此变得被动而消极。 有了“公平”这个目标之后,积极的国家还要担当起社会的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只要求公民的义务,没有权利。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如果一个穷人连过日子都很艰难,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尽子女教育的义务?就好比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能期望他对社会负责任吗?我的父亲半身瘫痪,他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负责,你能要求他对社会负责吗?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道理是一样,对于一个人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人,我们无法要求他对社会负责。国家必须在九年义务教育中担当起责任。但实际上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各县自己解决的。我想到了1993年实行的新税制,当然设想是好的,当初设计了收入转移机制,不发达地区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实际上,不发达地区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损了,因为基本上没有收入转移。中央拨给地方的资金跟着项目走,而要想接下项目,地方必须要有一定的资金配套,这个不发达地区是很难办到的。有一次我们到湘西访问,湖南省财政厅的一位副处长在会上声泪俱下:湘西历史上就是吃皇粮的地方,国家一直给补贴;到了现在,反而不进反出。湘西以烟酒业为支柱产业,国家对烟酒业征收特种消费税,此税是中央独享税,湘西因此出大于进。所以,1993年的财政改革让湘西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一谈到国家应该负责任,很多人会问:你是不是要强调国家干预?你是不是要全能的国家?当然不是。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国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的国家不是一个利维坦的全能国家,它承认自己能力的限度。借用森的话来说,这种态度表现的是assertive incompleteness,即用积极的态度来承认不完备性。那么,为与不为的界限是什么呢?国家作为的界限是为公民的能动性提供基本能力的保障,为公民提供一个起飞的平台。低于这个界限,就是消极的国家;超出这个界限,国家的作为往往不能成功,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粮食政策。 具体讲到三农问题,我着重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村庄民主,一个是农村基本社会保障。 很多人认为村庄民主意味着国家的退出,因此有“村民自治”的叫法。但是,这个词不好,这样一级级推上去,就是乡自治、县自治、省自治了,那么大家都自治?实际上,村庄民主是国家架构的一部分,是积极的国家的体现。但有人对村庄民主提出批评,认为民主是外来的,成本又太高;因为人口多,而且整体文化素质很低,选举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有人认为古代的乡绅自治的方法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管理成本低。他们没有看到,古代能够建立这种权威,是因为那时候具有权威建立的基础。一个是家族,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那样;另一个是知识优势,像白嘉轩的姐夫那样。但现在中国的农村不再具备这样的权威基础。家族势力已经很小了,有的地方即使保留祠堂,也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什么的,而不再是权威的象征。从文化层次来看,在比较发达的地方,也大都是初中毕业的水平。1950年代的时候,刘绍棠可以靠写书在北京买得起一座四合院,但现在就绝对办不到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刘绍棠的书贬值了,而是因为别人拥有的知识多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相对价格就要下降,就是这个道理。在农村中也一样,知识已经不能成为权威的来源。乡绅治理因此没有了社会基础。 村庄民主是建立新型的村庄文化的一个突破口。通过村庄民主来治理的成本并不高,投票率低也不是个问题。投票率低不能说明不民主,不能用投票率的高低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有的人不投票是认为谁当选都行:天下太平,谁当选都一样,这难道不是制度的胜利吗?村庄民主不应该向后退,而应该向前推进;不是做得过火了,而是做得还不够。现在是村庄民主可以叫做“孤岛民主”,因为只能在一村的农民之间实行,到了村外就不行了;而且,按照法律,村委会还要受党支部的支配。然而,现实正在冲破这种格局。广东省有一个村长,是选举出来的,得到村里的新兴商业阶层的支持,因此很有信心,敢向支部书记挑战,如不列席党支部的会议等。选举一年后,支部书记坦言,下届书记他不会做了,他要推荐全体村委会成员当党支部成员。 再谈农村基本社会保障问题。改革前一直实行的是合作医疗制度,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也解决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合作医疗制度靠公社财政的补贴,当公社垮台的时候,它也就随之垮了。现在农村有7亿人口,有医疗保障的还不到1%。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数字。农村识字率在公社时代提高很快,但近二十年慢了下来;全国的婴儿死亡率是32‰,发达国家是15‰左右。这个数字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不错的,但改革后的进步速度慢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一想农村有什么保障。经过多次改革,城市保障体系渐趋完善,建立了从养老、医疗到失业和低保等一系列社保制度;而农村却毫无保障。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健康调查,农村贫困人口中中因病治贫的比例为39%,有些典型调查发现这个比例更是达到70%。在座的农村来的同学大概体会很深,农村人生病,尤其是壮劳力生病,是一把双刃剑,不光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且还要借钱治病;欠下的债,几年之内是不可能还清的。农村大部分人毫无保障,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在土地上,国家给了农民自由。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朝着土地的事实私有迈进了一大步,它给了农民权利。但这还不够,国家还应该给农民使用这个权利的能力。这是国家应该有所为的。 当前,卫生部正在考虑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卫生部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恢复低层次的合作医疗。但我认为这不是个很好的路子。现在的农村都有私人医生,价格也都很低,就算有了合作医疗,农民也不一定爱去。一方面是出于不相信地方干部,钱在他们那里放着还不如在自己手里放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价格上也不一定能和私人医生竞争。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来说,合作医疗所能解决的疾病对农民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它不保那些对农民影响巨大的大病。如果以农民的需要为前提,首先建立大病保险系统可能更好一些。当然,这只是推测,还需要调查,有了数据就能更准确地说明问题。至于资金问题,国家至少要在初期负起责任。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农业税直接转化为保险基金。 总之,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就是要为农民的自我发展提供起飞的平台,其它的则不能做。比如提高农民收入,一时能起作用,但不能持久,因为国家财政有限,不能长期这样支持农村收入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政府要有所作为的是培养农村的造血能力,而不是只给它输血。 问题集锦 问:姚教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关于银行利率的问题。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是否应该放开? 答:这个问题比较大啊。我认为不光整个农村的利率应该自由化,银行的竞争没有利率的竞争就是少了一大块。具体到农村的情况,我认为在整顿农村金融秩序时,不能一刀切。像基金会,它是存在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被乡、村干部操控,贷款难以收回,这样储户怀疑,争相提款,就出了问题。而中国有这样的习惯:一旦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就不管好的、坏的一律取缔,有的做的很好,也被取缔了。应该容忍某种形式的民间金融的存在。在这么大的国家里,民间金融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像台湾,到现在民间金融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搞一刀切,就是把农村中的自主组织能力打垮了,又没有新的组织建立起来替代它,这样不好。 问:姚教授,您说要实行村庄民主,但是怎么处理国家与基层民主的关系呢?当出现分歧,不能直接上传下达正面体现国家精神的时候怎么办呢? 答:这正是我刚才所说的,村庄民主是国家架构的一部分。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正是孤岛民主和村庄以外的行政命令之间的矛盾的表现。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仍然是将民主扩大到村庄之外。 问:姚教授,农村土地是要每几年都分一次的,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呢? 答:矛盾不大。农村的土地是每几年都要分一次,但村庄有办法降低这个对农民向土地投资的影响,比如预留机动地、不调好地、补偿土地投资等。而且,我们还要看从哪个方面来看效率?是从土地与农业的效率看还是从整个社会的效率看?应该是从整个社会来看,看是不是有利于整个社会。双层土地所有制在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可能对整个社会的效率有好处。 问:姚教授,您刚才谈到国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那您能谈谈国家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应该做点什么吗?据我所知,义务教育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您怎么看待呢? 答:关于九年义务教育,国家不是没有投资,而是投资很大,但主要是盖学校、修路,对学校的日常运转以及农民的教育负担投资很少。有一次去贵州的一个村子做调查,村书记说,国家拨款建中心小学,但需要有配套资金,要求县、乡、村都要出一部分,摊到村里是2万元。但这个村只是个贫困的小村,2万元怎么凑得起来?村长就请求我们在北京给他们募捐,这件事最后就是靠募捐才完成的。我想,如果不是遇到我们刚好去调查,这所学校怕也是很难建起来啊!实际上义务教育的主要开支还不在建学校这一项,而在教师工资等日常开支,贫困县60%的开支是教育开支。这些钱都在当地解决,国家不负责。 问:农村改革几年来,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竞争:是包产到户好,还是不包产到户好?从效果和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来看,不包产到户的村要比包产到户的村好。我到过许多没有包产到户的村,医疗、教育搞得都很好。从理论上看,这该怎么解释呢?分田到户,积极性能调动起来,但不能实现规模经营;不分田,积极性不够,但可以规模经营、科技兴农容易实现。该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你的观察有问题,你只是观察了一个小样本。像你提到村子,都是样板村。这些村发展得好主要是起点不同,当时的集体经济就好,因此不想分田。再者是干部原因,一个好干部往往能带动一村人,而换上别的干部,可能这个村就会衰落。所有样板村都有一个能人干部。因此,这些村不分田,可能仅仅是因为分田之前就是一个好村,或因为集体工业的发展带动土地的重新集中;所以,不是不分田导致好的集体经济,而是好的集体经济导致不分田。我之所以说你的观察是基于小样本的,是因为我可以举出许多反例,比如广东就有一些分了田的村子,照样搞得很好。你的例子只是个例。借用张维迎批评有人对南街村的推崇时所说的,你不能因为某个断了胳膊的人用脚写字写得很漂亮,就要剁掉所有人的手。(笑) 问:您怎么看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呢? 答:进一步培养初中生对能力有作用,但作用不太大。应该多进行职业培训。 问:请您谈谈国家在棉花方面的“可为”和“不可为”好吗? 答:我对棉花的问题没有研究。但我想,同样的,国家也不能一味补贴,这样没有持久性。据了解,中国棉花的价格比国外高得多,而保持较高的价格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农民对价格有反应,价格高,农民就会多种,产量就会增加。我的观点是,国家要保持一定的粮食战略储备,但不能搞敞开收购。 问:您好!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学生,自己有很多的体会。在这里,我想先讲两件事。有个开发商到我们那里买地,本来应该是4万元一亩,但经这个开发商的活动,请客、喝酒,最后竟要以2万元的价格来成交。村里人知道后都非常气愤,我父亲他们到处去告,但现在还没有解决。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如何提高政府的信任度的问题。乡政府号召村民养猪,承诺包亏,但没想到固定投入和其他投入都已经投入很多的时候,猪肉的价格突然降了很多,那么多农民全亏本了,而政府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它依然什么都不管。您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拉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村集体不得擅自支配农户的土地,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一直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不是为了解决农业效率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农村政治问题。这位同学所讲的事就是一个例子。《农村土地承包法》明年三月份开始实施,到时候你父亲他们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个问题,你父亲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政府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它是没有能力替他们承担这个风险的。 问:您说国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那是不是有个原则呢? 答:当然。基本的原则就是国家为老百姓提供发展的平台,说具体的就是提供基本的保障和能力,让百姓不再为生病、失业而发愁。当然,在此之上也有可为和不可为之分,但要加以区分就不那么容易。在这里,判断是重要的。现在在宣传方工的事迹。依我看,方工的最大优点是会思考,以老百姓的常理来判断案件。大家都说要法治,但哪有纯粹的法治?法律是要人来执行的,因此“人治”不可避免。这时候就要求执法者要会判断,而符合老百姓常理的判断大概总是不会错的。 问:姚教授,我想请您谈一下,怎么样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待农业政策呢? 答:这个问题其实刚才都谈到了,新的法律不允许土地的调整;要想使新法顺利实现,国家应该为农业提供一定的保障。规模经营可以说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早在秦朝就只有欧洲的四分之一了。人口多,人均可耕地面积小,这跟美国是不能比的。美国耕地多,人口少,大农场的成本低,能够实现规模经营。但在中国不可能。如果规模经营,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怎么办?我们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实施规模经营就是浪费了劳动力。 问:您好!我想请您谈一下“非农化”的问题。谢谢! 答:非农化是一个缓慢、漫长的过程。“农村的出路在农村之外”,但这需要时间。我们不能走墨西哥的路,造成城市的恶性膨胀;也不能走发达国家早期走过的路,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把他们驱赶到城市里去。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各个城市排斥农村移民的理由。现在,大部分城市都意识到,离开农村移民,它们就无法正常运转了;但是,对于如何接纳农村移民,并使他们容入城市,却没有积极的措施。这方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北大乡土中国学会本学期系列讲座之三)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姚洋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