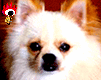孔子第72代后裔孔宪铎:躬行教育大半生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1日 19:13 中国青年报 | ||||||||
|
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起来只有两年,但最终他却取得了国外的博士学位,并先后担任过美国及香港两所大学的副校长;他已年近七旬,却重返学堂,成为北京大学一名心理学博士生,而导师整整小他30岁;像他的祖先孔子终身献身教育一样,孔家的这位第72代后人,在躬行教育的大半生中,仿佛真正感悟到了“子曰”的真谛 子曰孔宪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2500年前,孔夫子的这段人生感悟,仿佛正暗合了孔宪铎的一生。这位孔家的第72代后人,眼下正步入“从心所欲”的境界。一个月前,年近七旬的他,重返学堂,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博士生。 去年10月,北京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风波震荡海内外。此时,刚从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位置上退休的孔宪铎,被请到北京大学介绍办学经验。期间,他遇到了现任导师、北大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孔先生心血来潮,问:“能不能为我在哲学系安排一次讲演?我在思考‘基因与人性’方面的问题,想听听哲学家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孔宪铎就登上了讲台:“为什么子女爱父母,没有父母爱子女爱得深、爱得主动?为什么三个和尚会没有水吃?这些现象是否能用基因学的知识加以解释?” 一个半小时的讲演后,听者热烈鼓掌。王登峰兴奋地走上讲台,一个劲地说:“讲得好讲得好。你就来读我的博士生吧!就研究基因与人性。” 这次偶然的讲演成为孔宪铎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的初试。半年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参加面试。7月,他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正式拜在比自己年轻30岁的王登峰门下。 在常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孔宪铎看来,这丝毫没有“逾越规矩”。他经常说,年轻时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中年时做有责任必须做的事,到了老年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何况,孔家的祖训在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祖训还告诫:要“不耻下问。” 孔宪铎表示,读罢心理学博士,他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 显然,孔宪铎并不缺文凭,更不缺头顶上耀眼的光环。早在30年前,他就在加拿大取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洛杉矶大学读完了博士后。不仅如此,他还先后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身材不高,满头银发,面色红润。今天,当这位曾经的大学校长,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衫,和周围的人嘻嘻哈哈开着玩笑时,不太熟悉他的人时而会露出迟疑的神情。这时,孔校长就会一本正经反问:“难道我应该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吗?” 也许,这一切都是出于对54年前那个老气横秋的少年的青春补偿。那时15岁的孔宪铎只是一个偷渡客,孤身一人在香港纱厂做小工。不要说“基因”学,他连数学都没怎么学过。因为战乱和逃亡,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在一起,只有两年多。 有一天他病了。诊所里的人都用粤语、英语交谈,他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出现了。她不仅会说英语和上海话,还懂医学术语,主动帮孔宪铎做翻译。孔宪铎第一次感到了“癞蛤蟆与天鹅的区别”。 “你无法想像那种差别给我的刺激。”事隔多年孔宪铎仍记忆犹新。从诊所出来,他就去补习班报了名。他要成为“天鹅”。为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铎’(回)也不改其乐”。 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苦读4年,孔宪铎参加了台湾高校在香港的招生考试,并最终迈进台中农学院(今台湾中兴大学)的门槛。但起初他丝毫找不到“天鹅”的感觉。 试题中有“H2O”,他苦思瞑想,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因他压根没学过化学。大一时化学课照开,他借了本初中化学课本恶补,但要等到同学们都睡觉了,一个人躲进厕所的小间里,关上门偷偷看。 一次,孔宪铎问一个同学:“study是什么意思?”那个同学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惊诧地望着他:“这个词你都不知道?”他没敢再问下去。 终归不是“朽木”。凭着“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的刻苦,孔宪铎的成绩很快从最后几名升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持到毕业。一年后,他拿着朋友们资助的学费,去加拿大攻读硕士。几年后,又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到现在还不太懂微积分。”事业有成后,孔宪铎毫不掩饰,“我没学过。但我能记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 1970年,孔宪铎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转而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在植物生化和生理学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4年,他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正式聘用。 第一学期结束后,有个学生找到他,试图将成绩B改成A。孔宪铎翻到他的试卷,仔细看过后,说:“不能改。你的答案就是错的。”那个学生狡辩道:“不是我的答案错,是你说的英语我根本听不懂。” “我的英语真有那么糟糕吗?”从此,很少阅读非学术刊物的孔宪铎,开始大量阅读《读者文摘》和《花花公子》等通俗刊物,每个深夜都守在电视前看脱口秀节目,收集大量入时的笑话。 以后每次上课前,孔宪铎会先讲个笑话。学生们笑得拍桌跺脚,气喘不已。看着学生们兴奋的样子,他郑重提醒他们:无论是讲课还是讲笑话,我用的都是同一种英文。 执教3年后,孔宪铎升为副教授,又过了5年,他成为正教授,并相继在《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他的女儿曾抱怨,因为过于专注学术,这位学园艺出身的父亲,“把家里的花儿都养枯了”。 家里的花养枯了,但学术上的花却生机粲然。孔宪铎自豪地宣称:“在当时的植物生物学领域,我是最出色的10个人中的一位。我的学术论文,今天仍在被不断引用。” 正当孔宪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望时,他当年逃离的国度也开始走向世界。 一个中国学生写信给孔宪铎,说自己想出国留学,但没有钱。孔宪铎没有多想,掏出自己的钱,替他付了10所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费。虽然他们至今仍没见过面。 有位中国女学生经人介绍,辗转写信给孔宪铎,讲述自己赴美留学的愿望。她希望孔教授能借些钱给她。那笔钱不是个小数目,孔宪铎犹豫了。 “那些天我都没睡好觉,也不敢去办公室,怕看到她的信。”将近20年后,孔宪铎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只是出于“同情”。“其实是种责任感,是种罪恶感。数目虽然很大,但我也不是力不能及。如果我的力量允许,却不帮助她,那我……我就会有种罪恶感。” 从那时起,孔宪铎找到了自己“有责任而必须做的事”———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1978年,背井离乡近30年后,孔宪铎以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频繁回国。他吃惊地注意到:有1000多万人口的家乡山东临沂市,只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怎么能连一所大学都没有呢?”孔宪铎为此四处奔走。 经过多年学术训练,使他对数字有超常的敏感和记忆:“北京有1200万人口,却有大学67所,而临沂一所也没有;2002年,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北京、上海达到了48%以上,而临沂还不到1.7%;再看看周边的地区和国家:台湾的毛入学率是49%,韩国是52%,而美国是81%。” 孔宪铎最能打动家乡官员的一个观点是:“临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学,谁还能回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何能发展?”他向当地政府打包票:只要你们建起大学来,我帮你们找好老师。 这呼吁一喊就是十多年。喊得许多政府官员都开始“讨厌”他。这位本来令临沂人骄傲的大教授,一度成了“坐冷板凳的人”。 直到去年秋天,临沂大学才终于奠基。孔宪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奠基仪式。他虽兴奋但也不无遗憾:这是在临沂师专的基础上扩建的,仍然不是一所“新”大学。“我们不应为建大学而建大学,而是为了增加学习的名额,增加入学的机会。” 孔宪铎的好友、曾任临沂市副市长的綦敦祥直言相告:“不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钱呢?那可是一所大学呀!” 但孔宪铎认为这个逻辑不通:“2002年,全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已占GDP的3.41%,而山东占多少呢?”他坚持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科教兴国’,而应是‘国兴科教’。” 在家乡许多官员看来,孔宪铎的许多想法“不合时宜”,但当他的面,他们称之为“超前”。 3年前,孔宪铎从担任了10年的香港科大副校长位置上退休后,接受了山东建工学院名誉校长一职。在这里,他管了许多一般校长不会管的事。 学校的大门有两扇,却常常只开一边。这位名誉校长提出:为什么不都打开呢?校方答:门卫人手不够,怕不安全。“这不是理由。”他说,“不能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让进出的人麻烦。”两扇门都打开了,至今也没发生什么“不安全”的事。 学校里经常有人乱扔废物。孔校长找到校方,要求增加100个垃圾筒,并且要摆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学生反映打开水的时间太短,他立即向学校建议,早上和中午各增加半小时;甚至在世界杯比赛期间,他也要求学校一定要进行转播。 “我们办学校不是为了管学生,而应该是为学生服务。”这是孔宪铎担任近20年大学管理者的经验,“一切‘以人为本’,不能‘以管理者为本’。” 他任名誉校长期间,不仅以管琐事闻名,也常常因一些他认为很简单的事没有得到快速处理而恼火。 “我是个急性子。”孔宪铎解释道,转而又说,“在西方餐厅叫服务员时,他们答:我就来;而在中国,回答是:请等一下。这就是区别。” 相比上述所为,孔宪铎最“不合时宜”的想法,应该算是“乡村厕所改革”。 这个想法从1986年萌生。最初,他只是想推动“乡村厕所手纸运动”,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纸渐渐在农村普及了,他便把目光转向了厕所改造。 一次,孔宪铎去一所镇中学参观,这是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教学楼很漂亮,但一进校门我就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径直进去看,觉得“不堪入目”。 “培养人格要从尊严开始,尊严从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开始。”孔宪铎说,“就算从卫生角度考虑,也应该把厕所弄得干净点儿,至少要有水冲。” 当地人说,人吃的水都紧张,哪里有水冲厕所?更何况,室外厕所,冬季冲厕会结冰。 “因为两个月可能结冰,而让其余10个月都臭烘烘的?”孔宪铎不理解。 他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远虑”太多,因而失去了解决“近忧”的勇气。 “总会有办法的。”他回到香港,向朋友们募捐了约10万港币,准备选一所学校,建一个示范厕所:要有档板,有门,有冲水设备。 “一间厕所能改变什么?”有人不解地问。 孔宪铎想都没想回答道:“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可以建立人的尊严。这就是教育。” 庄子曰:道在屎溺。 孔宪铎表示,自己的一生结束后,他希望墓碑上不写博士、教授或校长之类的头衔,只写:“中国乡村厕所运动的推动者”。 (本报记者 江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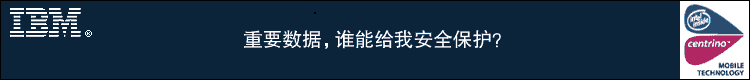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名师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