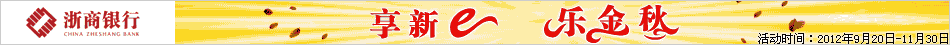北大国际卢锋:欧洲困境的深层根源
欧洲经济面临主权债务等多重多机困扰,但其深层根源与超主权货币内在机制局限有关。危机国外部债务相对规模过高是导致欧债危机的特征条件,由于积累过高外债需要一段时期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失衡,因而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不可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使欧元区整体失去治理失衡旧机制后又未能获得新手段。
基本事实表明,把部分欧元国拖入危机泥潭的不仅是通常债务负担过重,更为关键的是在债务结构方面外债比例过高以及“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负值过大。观察多国债务率数据可以看到,欧元区总体和欧元危机国债务率确实很高,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并非高得离谱。但是欧元区危机国通常外债较高。以2009公共部门外债占GDP比例为观察指标,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都在70%以上,较低者意大利与西班牙也分别在50%和30%上下。另外除意大利之外,2010年其他四个危机国国际投资净头寸负值表示的即国际净债务GDP占比高达90%-108%。
依据开放宏观经济学常识,一国特定时点过高外部债务存量,必由早先时期过高国际收支逆差流量累积转化而来,也必以本国实际汇率持续高估作为必要条件。因而要解释欧债危机真实根源,需要提出一个符合欧元区基本情况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实际汇率错配假说。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个失衡发生机制。第一,欧元成员国“竞争力差离倾向”,通过经常账户持续赤字派生外部举借债需求。第二,单一货币体制下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在一段时期为成员国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现实条件。两重效应配合作用下,持续外部失衡伴随持续外债累积,通过内外部环境演变,终于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下历史性达致“完美风暴”条件,并通过希腊这个南欧国家特殊而夸张的政治运作方式引爆欧债危机。
先看欧元制度下成员国“竞争力差离倾向”导致实际汇率与国际收支失衡情况。单一货币体制设计暗含一个前提假设:成员国劳动市场和其他实体经济参数会快速收敛,从而保证汇率与货币政策工具不复存在时,各成员国宏观经济仍能大致平顺有序运行。然而欧元区经济实际运行情况与上述理论假设大相径庭。引入欧元后其成员国之间工资变动差异显著。以2000-2008年德国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3%。考虑各国德国劳动生产率变动差异,同期五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德国上升幅度在25%到47%之间。
虽然单一货币定义性排除货币区内名义汇率变动,但是特定成员国单位劳动成本大幅增长,必然该国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数据显示,2000-2008年间,爱尔兰相对德国实际汇率升值约50%,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别升值27%,31%、34%和24%。与此相适应,2000年引入欧元后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希腊和葡萄牙年均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例高达9%-10%,西班牙在6%以上。并且这些国家逆差在2005年到危机爆发前呈现扩大态势。
再看欧元体制下“收益率扭曲效应”如何为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融资便利。经常账户逆差需要私人资本账户盈余或(和)政府外债融资保证平衡。通常情况下,一国长期经常项失衡难以在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得到低成本融资,因而融资困难对外部失衡和过度负债构成有效约束。欧元体制不对称改变成员国发债融资成本与能力:对德国这样竞争力较强国家影响较小,然而大大提升希腊等竞争力弱国举债能力。例如1993年希腊十年期国债相对德国利差高达十几个百分点,葡、西、意等国利差也在3-5个百分点上下,反应资本市场对国别经济基本面与风险差异的评估预期。引入欧元至危机前,各国利差普遍降至0.5个百分点以下极低水平,为这些国家过度债务融资大开方便之门。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中心国也一度分享到自己的那份利益。希腊等国负债增长给德国等国顺差增长提供需求条件,德国净出口占GDP比例从2000年不到1%增长到危机前6%-7%。类似于区域性排他性自由贸易区具有“贸易转移效应”,欧元体制对区域内金融市场投资引入“欧元偏向效应”,加之欧元在区域外作为国际货币影响力加大,欧元中心国金融机构得以快速扩张。
由于欧元体制客观上给部分成员国家同时提供了外部债务融资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因而实施超主权单一货币后欧元区整体新发债券规模快速膨胀。数据显示,欧元区新发债总额趋势值在上世纪90年代十年间增长不到一倍,但是2000年欧元问世到危机前不足十年间增长4-5倍。如果说华尔街投行金融家用次贷-次债这类负债金融衍生工具为美国经济挖掘陷阱,欧盟精英则以欧元体制宏大设计把欧洲经济引入过高杠杆化的危险境地。
欧元体制一段时期为成员国带来皆大欢喜的扩张盛宴,深层隐忧是各国财政独立基础上货币联盟成员国具有吃大锅饭和搭便车冲动,由此可能造成赤字和债务过高的危机风险。欧元战略家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引入事先与事后规则加以防范。然而事实表明这些规则都不能达到设计效果。
按照事先规则要求,申请加入欧元国家必须在赤字和通胀等宏观指标上达到一定标准才会被批准成为成员国。认为加入欧元有利可图国家总能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达标,使得事先限制条件难以真正把潜在“问题成员国”挡在单一货币外。例如据后来报道,希腊当年加入欧元,就多亏某个国际大投行指点,采用涉嫌造假手段方获成功。事后规制包括1997年通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财政赤字和债务阈值。财政赤字超标需在一年内纠正,连续三年超标则需按程序上缴不超过相当于本国半个百分点GDP的罚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2-2004年德法两国率先触犯红线,却以自身特殊影响力绕过规制免受责罚。昭告世人规制形同虚设,“稳定公约不稳定”。
欧元体制在内部埋下可能引爆危机地雷的同时,还取消了采用常规手段应对炸雷事故的可能性。拥有主权货币国家万一因为宏观管理不善或其他冲击出现双赤字困难,至少还可以通过汇率、利率和财政等多方面手段加以应对。超主权货币一劳永逸地取消了成员国通过汇率利率等相对价格工具调节失衡与应对危机的可能。
特定共同体应对债务危机另一逻辑可能性,是成员国减记甚至取消债务存量。就欧债危机而言,高债务国主要是对其它欧元“兄弟”成员国欠债,欧元区整体外部负债不多。如果德国等主要欧元区内债权国真的愿意施以援手,欧元区应能自行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甚至欧债危机本身就不会发生。但在现行欧元模式下,这条路也崎岖难行。欧元货币一体化孤军深入造成一个跛足体制:货币同盟这条腿已大步迈出,财政集中这条腿却未能跟进。欧盟目前预算盘子仅相当于区内GDP百分之一。几年前“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公投闯关”失利,意味着在税收财政和转移支付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将遥遥无期。通过财政手段调整存量应对危机,也因缺乏相应制度安排和政治意愿难以实施。
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史事件。观察欧债危机后三年来若干“欧猪国家(PIIGS)”国债利差演变情况,可见欧债危机在波动起伏中总体呈现深化趋势,也说明在现行欧元体制架构没有大刀阔斧改革前提下“救助换紧缩”应对方针难以奏效。欧债危机根植于欧元目前机制局限,人们寄希望于再造欧元以根治危机,但又知易行难并阻碍重重。即便在一组不坏假设条件下,欧洲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可能难以摆脱低速增长和濒临衰退状态。如果发生个别欧元区国家退出甚至更为剧烈的欧元重组情形,则难免剧烈震动和严重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