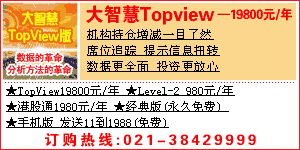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知识分子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2日 21:27 《管理学家》
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知识分子 作者:马龙行 经济人理性的滥觞 有人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济人理性是现代经济学的公理。既然是公理,本身就无须证明,更重要的是不允许有例外。如果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一下验证,我们就会知道此言不虚。中国经济学家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热衷于验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等等,都是经济人理性的明证。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家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们在自觉地维护着经济人理性,存在着主观故意,是方法论中应该排除的当事人或者说叫利益攸关者,那么,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的经济人理性。维护经济人理性的基础,就是维护整个现代经济学宏伟大厦,就是维护这栋大厦的主人们经济学家的利益。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是学到了祖师爷的精髓。 但是,也有个别冥顽不化者。天真的邹恒甫先生似乎有些孩子气,几个月来像堂?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批评以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不务正业只为稻粱谋,企图以个人之力对抗中国经济学家整个群体。网上双方各有一批拥趸为心目中偶像和英雄论战,虽然说现在有一方好像占了上风,但联系到现实中完全相反的双方力量对比,孰是孰非,依然让人有如雾里看花。 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邹恒甫本人也是在实践经济人理性,这没有错,但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没有事实可以验证的含义,没有解释力。就像你可以说一个人自杀,是经济人理性,是因为死亡对他来说更便宜,他可以不用还毕生也还不清的债务,他可以不用忍受自己认为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和恐惧,等等。只是,我们还是可以质疑:生还是死,只是一个问题吗? 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是万物之灵,是大地的主宰,替上帝管理这个世界。人堕落之后,自己的欲望成了自己的“上帝”。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欲望(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先满足低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当一个人存在多种需求时,总是缺乏食物的饥饿需求占有最大的优势;当一个人被生理需求所控制时,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都会被推后。有人认为,中国人都穷怕了,所以生理需求的满足尤其重要,中国经济学家自然也在其中。邹恒甫是因为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久了,腐败惯了,所以他的生理需求才显得不是那么迫切。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学家自然会上升到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高级阶段。有人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不但是在误读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需求的定义,而且是在强奸中国经济学家的民意。君不见,中国经济学家们正在努力把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有人说:存在即合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关键在于“理”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哪个“理”才是合理的。法西斯从人类普适性价值观上讲是不合理的,但它既然存在过,就说明它符合事物发生的规律,它消亡,也是在事物消亡的规律中消亡。所以,如果我们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我们永远不可能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有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解,用市场来解决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且不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对错,市场本身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过程中就有缺陷。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会集中并导致垄断,垄断自然不会是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和学官的权力,垄断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阐释权;他们利用政府与企业,垄断了资源在经济学家中的配置权,以“劣币驱逐良币”。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是以西方良好的道德法律制度为前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缺失、道德沦丧的时代,难道我们只能在等待人们的良心发现与坐以待毙中进行选择? 有人论证说,经济学家追财逐色争名夺利的个体经济人理性,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最终将导致每个经济学家的利益受损。经济学家的名声在大众中越来越臭,有人甚至断言,近几年来,经济学家在事实上正在被边缘化。有网友更是大胆预测,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会被社会遗弃而被迫退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舞台。其实,用不着我们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利益担忧,他们更清楚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辩证关系,也比我们更加关心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他们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是高明之极。也许,他们的心里在想:人生不过百年,在我之后,哪怕他洪水滔天…… 直觉告诉我们问题的存在,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解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伤的是谁? 孙大午先生说:富人不是靠经济学家致富的,但经济学家致富都是靠富人。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孙先生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经济学家与富人更多地是在共同富裕。在这个以金钱为主要量度来衡量人的能力的时代,事实告诉我们,创富的英雄们绝对不是活雷锋,更不是傻子。那种把富人当傻瓜的说法,我们只能认为要么是置事实于不顾,要么是一种酸葡萄心态。富人和经济学家,更多地可能是出于彼此的需要而结成了致富共同体。在这个乱世快钱的时代,期望企业进行规范化的商业运作与管理的想法,只能被人认为是不懂企业、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所以,批评企业没有弄清楚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区别,认为是企业请错了人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企业的需求,“子非鱼,安知鱼之需”?企业可能需要管理学家,但更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忽略经济学家们的专业知识所能给富人及其企业带来的些微创富帮助,即使是他们的话语权和身上经济学家光环,通过富人的个人能量及其企业的放大作用,都可以带来许多有形无形的好处。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都是社会成本,减弱了公众的社会福利。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要润滑剂,能够促进改革。无论如何,公众都是被蒙蔽的对象,都是弱者,也只能做弱者,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渠道。我们讨论“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的问题,结论却倾向于断定这是一个伪命题。双方当事人虽然各怀鬼胎,但都乐在其中。 呼唤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的期望很清晰。按照邹先生的建议,经济学家们回归象牙塔,做阳春白雪的学术,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犹如过江之鲫巨大基数,等到一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履平地之时,那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毫无疑问,邹先生是爱国的,邹先生的期望是美好的,邹先生作为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是非常看重自己的职业的。但是,邹先生的期望,显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更不是公众的迫切需要。中国社会,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经商的眼红读书的,读书的眼红当官的,当官的眼红经商的。乍一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今的三种人都是志得意满顺风顺水的,哪有红眼病的征兆?再一想,款博、学官、官商已经到处泛滥,哪还分得清是三种人,分明是一种人嘛,自然谈不上谁眼红谁。可是,相对于三种人融为一体后的个个脑满肠肥,公众并没有切身感受到GDP数字上的快速增长。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传统上对知识的尊敬,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为他们说话的明事理的“文化人”,也就是知识分子。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知识分子”被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公共知识分子则被认为是超阶级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人类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西方是通过先哲设计的互相制衡的基本制度,亘古以来人类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从制度、法律、宗教、道德、舆论等各个方面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信仰缺失、制度不完善的中国,在一个转型期社会里,公众都有一种强烈的需求,需求专家对于某些事项做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媒体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专家的依赖似乎也越来越强烈。公共知识分子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发出的独立声音,弥足珍贵。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中国经济学家在发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威力,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自然而然地承载了许多中国大众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好期望。诚然,经济学家有选择做不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由;诚然,在道德上,为公众利益代言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比为某个利益集团代言的同行更优越;诚然,经济学家是科学家,应该首先尊重的是科学事实;但是,请你首先表明或者界定清楚自己的角色。经济学家不是通才,不是“十全老人”,定位为科学家者,就应该在面对大众媒体的公共问题时免开金口。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者,就不能处处为了一己之私利。滥竽充数者的道德自然被人们的质疑。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不乏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很多经济学家发出了自己独立的积极声音。事实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经济学家的科学家身份并不一定冲突。现在不是非常年代,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缺少的只是心灵的净化。 经管分家 作者:莫士 “在管理领域,经济学家要清楚自身的局限,不要‘手里有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教授的话似乎为喧嚣的经济学界浇了一盆凉水。 经济学的繁荣伴随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各类资本市场逐渐渗入日常生活,经济学开始走出大学校园,成为“显学”。当发财的梦想开始与普通人紧密相连时,当“看不见的手”取代“看得见的手”成为市场主流时,能够把握市场脉搏的经济学家成为大众眼中的明星。人们首先知道了老一辈的吴敬琏、厉以宁、董辅 ,后来又知道了中生代“京城四少”那一辈的钟朋荣、刘伟、樊纲、魏杰、林毅夫、杨帆等,再后来便是新生代如日中天的张维迎、郎咸平。 “存在即合理 (existence in possible)”,时下经济学家的“热销”自然证明了其生逢其时。大众顶礼膜拜、企业奉为上宾、媒体连篇累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全民娱乐时代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透过光环的层层晕环,我们发现喧嚣背后的悖论。 经济无处不在,经济学无处不在,经济学家却不能无处不在。这就如同物理定律影响万物,物理学家却不可指点江山一样。世界本身就是一体,各学科的区分是专业分工的结果,如果各学科中所谓的专家屡屡越俎代庖,恐怕难免贻笑大方。 经济学之于管理学,如同牛顿力学与量子物理,前者宏观,后者微观;前者仅仅将企业视为经济规律下既定的变量,后者却将企业视为研究的全部;前者力图求得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却在追求单个企业的最大利润。 但是,从市场营销到企业战略,从人力资源到组织管理,似乎在所有管理领域指点江山的都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数条。 其中之一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管理学家的稀缺。相比于经济学的严谨理论与坐而论道,管理学无疑更偏重于实践操作。无论是早期的泰罗、法约尔,还是今天的德鲁克、韦尔奇,他们所拥有的不是严谨的数学推理、精妙的模型,而是在企业中长久的观察、实验,如同经验方程相比于理论方程。所以,相比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更难成长,也更难以复制自己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当一大批经济学家能够在改革开放后留洋学有所成时,管理学家的成长周期却远未达标。 此外,中国独有的国情让经济学家能够更为企业所倚重。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所以政府指令的影响力与不可预测性都超过了西方国家。而在西方的管理学家眼中,政府的法令即便不是既定变量,也不是他考虑的主要因素,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考虑在市场与企业的交互作用下,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当今中国急剧变化的市场却无法给予中国管理学家如此稳定的市场环境。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改变自身的收益可能远远小于改变环境的收益,所以它们将主流经济学家奉为上宾,期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影响政府决策。我们看到活跃于各大企业的经济学家无不拥有强烈的政府背景,曾任人大经济系主任、国资局科研所所长的魏杰,曾任职中央办公厅的钟朋荣,曾任职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樊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虽然种种原因造成了现今中国经济学家的热销与管理学家的难产,但是如此剑走偏锋的形式终究不是常态。中国经济最终将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与国际对手正面过招。寄希望将国内市场不规范的做法应用在国际市场上,无疑将会头破血流。所以,当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大时,中国的经管分家亦当开始,各司其职,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