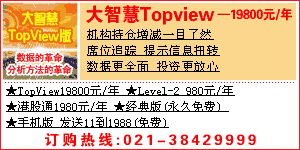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华生:不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2日 14:35 《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周颖 特约摄影=李果繁 身负“黑五类”家属的帽子,从15岁到25岁,近11年下农村进工厂的这段经历,形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农村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也树立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使他看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与众不同。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学院派的条件,是既从书本也从实践中学习的经济学家。 今年10月15日,当股指冲破6000点并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一些理性的投资者们却担心市值过高而出现更多的泡末。很多投资者甚至包括一些业内人士都想到了一个人——华生。 尽管华生不是股市的神明,但2001年和2005年,两次准确地预言了股市走向之后,他对股市的分析判断似乎成了更多投资者的风向标。 事不止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华生和他的同伴们就先后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竞聘企业经理人的建议,这些思路深深影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华生对股权分置的精辟观点和独到深入的分析再次赢得了市场的认同。应该说,这三次的重大学术成就,也是他人生之路的真实写照,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生于1953年初的华生,具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征。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到研究资本市场,华生的经历似乎是中国改革开放浓缩的一个个人背影。阅读华生,也是还原那一代人真实的历史,并还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那些闪光的碎片。 “其实我不很自信。” 10月19日下午1∶30分,在北京北四环边的办公室里,《数字商业时代》的摄影师在为华生拍照,一再提醒他表现出更多自信的笑容时,他却做出了如上表述。 “也许是青少年时代‘黑五类’经历的影响,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怯生生地看着公社大院的神情,所以好像成了习惯,摆不出什么样特别自信的神态。”华生说。 1966年,13岁的华生从江苏步行来到北京。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全国的大串联活动,因为他头上有一顶“黑五类”子女的帽子。 1968年,上完初二15岁的华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并且到农村插队,这一干就是5年。期间,他当过一年的生产队长。在当时的环境下,寻找读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是马列全集、资本论等,于是,人们常常能够看到坐在田梗上的华生,手里拿着这些厚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 五年以后,他转到当地工厂当工人,担任过车间主任。这又是一个五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华生才离开工厂,真正走进大学校园。 然而,正是这段经历,却对于他发现社会、发现社会资本形态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直到今天,提到当年的境遇,华生没有太多的怨言,而认为正是当年的经历才使自己有丰富的思想,正是改革开放才使他有好的机遇。 “15-25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使自己不会坐而论道,不会不切实际。不管是西方的东西,还是对社会的了解,你有求知欲,你要了解所有东西,但是,你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从学校到学校,从机关到机关,那么你的思路不会这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会这么想问题?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和那些年的生活背景有重要的原因吧。 近距离接触华生,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亲和、用平实的语言阐述经济现象时能让所有人读懂的经济学家。 当时可以说是在田梗上读完了马列全集、资本论。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个人的历程和你们这一代人都很相近吗?有什么特点? 华生: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吧,我也许只是更典型些,所有的事都赶上了。文革的时候我13岁。1966年,因为那时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不准参加大串联,所以我从江苏步行来到北京。1968年,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很快插队到农村,一干就是五年多。后来又到当地工厂工作了五年多。1968~1978年将近11年的时间我都在农村,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在财贸所和经济所工作。应该说,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是“黑五类”子女,生活很艰难,那个时期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后来读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才有了根本转变。 DT: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选择经济学的? 华生:选择经济学其实是有原因的。1968年我下乡的时候刚读完初二,初中没有毕业,基本上是下乡时在农村开始读书的。那个时代也没什么书可以读,书太少了,全都是一些马列著作、资本论之类。因为基本的生活环境是在农村和工厂,所以很自然就对农村、工厂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DT:在农村和工厂这段时间,你有时间读这些书吗?你自己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华生:当时可以说是在田梗上读完了马列全集、资本论。虽然学了很多东西,读了很多书,比如经济学、西方哲学、社会主义起源等,都是沿着这个线索去学的,但当时的思想不是很成熟,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有片面性。那个时候思考的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社会究竟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但并没有形成很清晰的想法。 DT: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经历对你进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帮助? 华生:我上山下乡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儿,15~25岁的黄金年龄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但对我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一是没有完全浪费时间,在田梗上读了很多东西,另外最主要的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这也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很快融入到改革开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我参与了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讨论,而且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曾经提出的几个想法针对中国特点,富有中国特色,后来基本上都变成了决策。我想这些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因为长期和农民工人打交道,和他们的感情相通,想法也相同,所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会有很深刻的认识。 不管是对西方,还是对中国社会,你有求知欲,都想要了解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必须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DT:1968~1978年正是你15~25岁的黄金年龄,这期间你在农村、工厂,那么,在你进入大学校园后,你的人生观会有改变吗? 华生:好像没有,但还是在发展、形成吧。读大学、读研究生,包括后来出国留学以后,视野更开阔了,认识问题会更全面些。 DT:你之前阅读了很多关于资本方面的书,真正对经济有感觉是在什么时候? 华生:1977年开始,气候慢慢变暖,我就开始了解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一篇经济学的论文。文章是1978年考上大学之前在工厂写出来和投寄的。这和当时直接进校门的大学生不一样,毕竟已经成年,有了多年的实践和积累。那个阶段还是大锅饭时期,这篇文章我现在看了也有点惊讶,当时谈的不是工厂管理,谈的是资金要有偿使用,应当采取资金利润率去考核企业。 DT:1978年恢复高考,你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你个人是怎么和这个大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的? 华生:我那个时候主要是恶补数学和英语。因为我在高考的时候这两门功课都不及格。别的知识都很好,尤其是社会知识,但就是这两门功课不行,数学不及格,英语26个字母都写不全,所以不守规矩,去数学系听数学,跟英语班学英语。贪婪地求知。大学,研究生,后来还去英国读书。所以说我是一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的受益者。 DT:你刚才谈到受益的角度,如果从参与的角度来谈,你又参与了哪些事情? 华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改,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当地县里的工厂里,也上不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来到北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有机会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前沿的东西。这有一些偶然因素,因为我的导师们都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当时百废待兴,会议很多,这样就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等工作。 从参与的角度来说,记得1982年来北京不久,就参与了中央银行(当时叫人民银行)改革研讨会,与人行的领导对话,那个时候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跟领导也敢争论,后来我的导师还去致歉。当时运气比较好,正好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 再有就是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即莫干山会议,我的论文入选之后,被邀请去开会。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五个研究生同学搞了个放调结和的价格双轨制,受到会议的肯定,如果没有大家的思路碰撞,也产生不出双轨制,因为我们的想法不是从家带去的。 20世纪80年代是时代的机缘,有人说是声望的顶峰,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确实都有,那是一个历史阶段。 DT:当时你有两件很自豪的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价格双轨制,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参与这件事情的? 华生: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年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同志感受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一个大的突破,需要一些对策性的意见,因而用征集论文的方式网罗人才参与。记得王岐山、马凯都是会议的核心组织者。我们都是因论文入选参会。当时我入选的论文写的不是价格方面的问题。 会议价格组围绕价格改革的思路挂牌通宵辩论,吸引了其他各组来观战助战。论战先是围绕以调为主(大步调整或小步快调,田源、李剑阁为代表),和以放为主(张维迎为代表)展开,争了一二天,没有结果,后来我和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几个人,也都是研究生,提出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即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 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也不知会议有什么背景,凭入选论文参会,满腔热情地为改革建言,大家都毫无顾忌,没有偏见,得理不让人。时至今日,大家一提莫干山,都记得当年挑灯夜战,挂牌辩论的场景。 DT:后来你还提出过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的问题,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华生:双轨制是1984年搞的,1985~1986年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因为莫干山会议后,我就较多地参加了关于改革的会议,被推着要从改革的全局上思考一些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底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主要内容,1986年初分期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 DT: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命题作文还是自愿的? 华生:不是命题。那个时候是团队作战,最后由我执笔。报告在1985年很快出来了,之后拿给领导看。当时我们就提出:国有资产的管理要有责任人。因为根据中国的情况,承包只是短期的做法,不是一个长期的出路。搞股份制也要有投资人,国有资产到底怎么管?我们建议要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评估、考核和受益分享,同时竞聘企业经理人,不搞行政任命。 这个改革,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当时提出国家要把所有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划到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要对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负责任,就是说国有资产要有责任人。 国家要以出资来参与企业利润分成,这是今年国有资本要搞的事情,还没开始。当时提出的全面竞聘企业经理人,而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下设,预算可以按照经济区域划分,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这些到今天都还没有做到。 DT:这之后,是不是参与度就更高了? 华生:后来我参与了国务院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当然会议就更多了。那时候国务院经常打电话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我们几点几点到国务院会议室去开会,对当时那样的年轻学生、学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学习和参与的机会。 DT: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你上大学以来的第一个人生顶峰吧?你当时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 华生:20世纪80年代是时代的机缘,有人说是声望的顶峰,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对学术界的影响力,确实都有,那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并没有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也来不及考虑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有想过别的。我见过那么多领导,但说和某位领导拉拉关系,以后谋个一官半职的,这个想法那时根本没有。在国务院开会,领导当然都会见到,但是都很自然,气氛宽松,只是研究问题。 当你该想怎么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你的思维调不过来,因为你本来不是干这个的。 DT:后来你为什么出国了,有其他原因吗? 华生:就是去牛津大学学习,这是很正常的。我1987年初开始出国,1988年回来半年,1989年1月出国,后来又去剑桥大学工作,成了众多海外学子的一员。90年代中回来以后,发现国内变化很大。 DT:出国之前你在社科院工作,回国后为什么没再回社科院? 华生:因为我被除名了。我是1989年1月留学的,当时被除名有多种原因,说不清楚的,找个理由就被开除了。好像是1990年或1991年被开除的。社科院还把除名通知书寄给牛津大学校方,牛津大学看到这个东西,哭笑不得。 DT:这是你后来下海的主要原因吗? 华生:回来之后我的房子被收了,工作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要吃饭要谋生,不得不下海,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了。 DT:之前你有想过下海经商吗? 华生: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想过经商,因为我不适合经商。别人怀疑我,我也怀疑自己,我从来不会经商,因为我是学术思维,得理不让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还是下海了,否则你就出国。虽然我有英国的华侨身份,但我不愿意出国,不愿意长期留在国外。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你的根就决定了你在国内,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发挥作用。当然有海可以下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如果是计划经济,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了。 DT:当年下海的时候几个人,你们主要做些什么业务? 华生:当时我下海的时候就两个人: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才慢慢做起来。一开始我们主要从咨询、第三产业做起,因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因为没有钱,当时我们引进ISO9000,中国需要这个,这是英国最先发明的,后成为国际标准。我们也曾经开过餐馆,但倒闭了。 推动国内引进ISO9000、ISO14000等国际标准,我们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开拓者吧。这应该和留学经历、海外背景有关。后来有人问我下海的经验,我说很重要的就是开头别有钱,这样你犯不了大错误。 DT:到后来你的企业规模有多大? 华生:几年下来就有了一定规模,员工也很多。吃饭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是要把企业做大,做成一流企业,我的思维就不行了。遇到问题我总会想,这个政策好像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定。思维总是在这方面有局限。当你该想怎么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你的思维调不过来,因为你本来不是干这个的。 DT: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下海,也有很多被淹死的,你怎么能够幸免? 华生:这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一流的企业家都有他的卓越之处,这是天赋的,我认为自己肯定不属于这种,但也还有一点儿素质。如果完全没有,做起来也不行,必须具备那种敏感,那种把握,那种决策能力。所谓商场如战场。 另一方面,这和我过去在农村、工厂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虽然是书生,但还不完全是书呆子吧,知道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除了这两点以外,我还有海外知识和信息的背景,这也是我能幸免的一个因素吧。 DT:你下海这几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关注资本市场吗? 华生:开始前两年,我几乎不读书不看报,光顾着生存了。后来大致从1997年左右,我才开始慢慢关注股市,并且做些这方面的分析研究。 DT:后来你的公司交给别人打理了吗?你的下海经商经历,对你研究资本市场有帮助吗? 华生:是的,有一批同学打理。我们公司的领导班子都是同学,包括大学、研究生、博士的同学,像个同学会。 这段下海经历对我很有帮助。我经历了教科书上所说的经典的发展模式:个人—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我还当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我发现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是想着大家赚不赚钱的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股市的结构和制度。 DT:到底是什么原因,又使你开始关注、研究中国股市,尤其是在股权分置方面,你有大量的思考呢? 华生:大概和我在英国的经历有关。我对金融有研究,既有实践也有理论,但我在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买股票,却赔得很厉害。回国后留了两只英国的股票。没想到这两只股票反而让我赚了钱。 回国以后,我发现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是想着大家赚不赚钱的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股市结构和制度问题。之所以能提出股权分置,这和我在西方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能做不同市场的比较,否则你怎么能看到它的缺陷?有比较,有分析,再抓住主要矛盾,这样就在1998年初发表了股权分置的文章,提出这个制度缺陷必须改革。 DT: 2001年6月你写了一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事实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当初是基于什么判断得出这个结论的? 华生:我当时对熊市的判断,主要是跟股权分置的理论有关系。在大家还不接受的时候,我就认为,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问题,而国有股减持一推出,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差别,因而必然会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这样流通股价要大跌,就是股市要大跌。我认为这个错误如果不改,将会给中国股市带来一场浩劫。虽然我的这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话说得很绝对,但我确实有这个理论信心和勇气,因为毕竟从1997年开始,在没有人重视和承认时,我一直在研究这个股权分置问题,研究了四五年。 DT: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障碍,或者一些质疑? 华生: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都不发,寄给南方一家有名的报纸,也不发。实在没办法,我在自己主办的刊物《时代财富》上发了。出来以后,谁也没有转载。有一次我出差,在飞机上看到《中国民航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我还很欣慰,自己安慰自己,看来还有人识货。 DT:那么2005年《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你又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华生:当时我的判断依据还是部分的和我对股权分置的判断有关系,因为股改拉开了序幕。当试点方案推出来的时候,被整个市场认为是灾难,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拉开序幕,是市场转折的标志,是牛市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实际上这两次的观点不是说谁能神机妙算,只是说如果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就会准确些。 DT:作为学者,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成长周期包括其中的很多起伏? 华生: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起伏。一个人要抓住机遇。抓住机会,也不是偶然的事情,需要积累和沉淀。我觉得在80年代,自己机遇的成分更大些。比如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的智慧碰撞出来的,赶上改革开放的需要,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这个东西。90年代以来,努力的成分更多些,因为时代发展,大浪淘沙,你必须从头开始,接受历史的重新检验。 其实如果围绕一个问题研究,能说透就不错了,不能什么都谈。 DT:你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什么? 华生:除了资本市场以外,有几个大问题:一是从前年开始关注城市化和新农村的问题,二是国资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来,尽管还没全做到,但要研究下一步的走向。当然,我也关注一些宏观经济问题。 一般来说,我做东西比较专注,不会对很多问题发表意见。比如从1997年来重点就研究了一个资本市场。其实如果围绕一个问题研究,能说透就不错了,不能什么都谈。不能有一个热点就发表意见,什么都懂,我反正是不行的。 DT:你的业余生活都有哪些? 华生:我总是有干不完的活。业余生活体育锻炼主要是打打乒乓球。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做别的事情。我的生活简单,主要是阅读写作,读一些经济、政治、哲学、文学书籍。 当然因为铁凝(华生的夫人,现任中国作协主席)是作家的原因,我会多读一些文学,现在我对文学的关注比以前更多了。生活在一起总会有影响和互补。我喜欢和朋友交流,但不太习惯到社交场所,学术的研讨会我还是经常参加。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