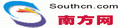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
|
梁从诫:绿色中国推动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三十而立·倒评年度人物】
梁从诫1994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精神源头。
他开展了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保护藏羚羊与可可西里的反盗猎行动。
他和自然之友的呼号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注意。
1994年,环境恶化的阴影正从四面八方潜行而来。梁从诫是先知先觉者之一。80年代,一封写给《百科知识》杂志的来稿使他意识到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这一年,他和另外三位同仁创办了“绿色环境文化协会”,大家在私下将其简称为“自然之友”。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NGO之一,为打破政府垄断社会公益资源配置的格局迈出了第一步。
英国首相也被他打动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支持并在第二天会见了他。
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以维持其运转的花销。梁从诫还以67岁的高龄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 站在山口,他说:“我们像是回家了。”话刚出口,“野牦牛队”那帮剽悍的康巴小伙子竟然哇地哭成一片。
但是,在这些打动人心的故事背后,梁从诫与“自然之友”做得最多的却是琐碎而重复的事务。在筹集资金扶持项目外,他对环保知识与理念的普及更是身体力行。
日常外出,他坚持骑自行车。有一回他骑车去政协开会报到,门卫拦他:“你给谁报到?”“给我自己。”门卫不信,他掏出委员证才进了门。
梁从诫曾应邀到一国家机关演讲,那天,只有5位听众。梁从诫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昆明的会员王愉,在自己的大学里搞了个绿色社团,会员已达几百人。她写信给梁从诫:“当年你到我们学校演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小树林。”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在“自然之友”看来,能不能、敢不敢真正监督政府,对后者提出实质性的批评和建议,是独立NGO和由党政机关衍生出来的NGO的一个重要区别。他们想在此开辟出一条可行之路。
但梁从诫也清楚在中国做NGO的局限,在监督之外,他还将“自然之友”定位为温和的合作者。
尽管如此,“自然之友”依然饱尝世事艰辛。“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的,如果碰巧改变或者纠正了,那纯属例外。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败多胜少的战斗。”梁从诫的一位同事说。
梁从诫常有无力之感。“我们是一群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曾总结说。
梁从诫的祖父是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一代才女。而梁从诫本人亦是全国政协委员。这样的特殊身份帮助了梁从诫和他的“自然之友”,尽管这并非他所愿。
“自然之友”的成就,已经很难说清这是梁从诫的个人贡献还是“自然之友”的集体成功。诸如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都是通过他的政协委员提案渠道才得以递交。
这样的渠道,虽然为“自然之友”的工作提供了方便,但也成为梁从诫的隐忧:“我梁从诫也总有走的一天,‘自然之友’不能上演‘人亡政息’的悲剧。”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已受到更多的重视。一次,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惟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非梁从诫。
而在更深远的时空中,“自然之友”激发了环保主义者的行动热情。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从一元化的计划经济向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从一部分社会领域逐步退出,NGO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逐渐成型。
现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民间NGO已遍布各个省市。梁从诫曾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他的愿望正在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