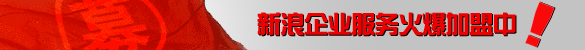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您在今年3月刚刚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像您这样的权威经济学家的文章(《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借助互联网传播?
刘国光:这个谈话的来历,是今年7月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同志到我这儿来聊天,一聊就聊出七、八、九个问题,他记下来并整理了出来,还是一个初稿。他们
自己有简报,马上就发了。上报中央的同时,他也发到网上去了,有好几个网站,我事先并不知道。说实在话,我还不是很熟悉网络,也不知道网络的作用有多大。但是传播以后并不违反我的意思,我也不反对。
《经济观察报》:经过网上流传,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刘国光:我谈的这些意见,应该说有相当多的人还是很赞成的,很多地方都是晚上电话议论,开会研讨。至于网上的流传,我说我不反对,同时我也没有寄托于那个东西。但是引起的波澜之大,我也没想到。这完全不是个人的能耐,而是问题牵动人心。
《经济观察报》:您在文章中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比如说,您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
刘国光:这篇文章后来公开在《高校理论比较》第九期和《经济研究》第十期发表,删改了,缓和了一些,但还是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大都是我的学术界朋友。我也不是有意要得罪这些人。我是在讲一些事实,我引用的人与事,都是有根有据,至于引用的合适不合适,是个人判断,但事实就是这样的。确实有这些事情。不过,我很欣赏和尊重作为学者的他们。我们只是观点有些交叉,这没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您在1979年就深入论证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1992年十四大前就明确提出用市场方式取代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是您今年中国经济学奖的“答词”出来后,一些人不明白,一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着深刻认识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
刘国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我曾作过多次论述,我在“答词”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观点。我说了“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说了市场也有缺陷,不能迷信市场。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病和市场经济的好处,我过去讲的好像不比谁少。但是,当然,话还要说回来,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不敢像有些人那样自信自己一贯正确,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贯正确。过去,在感受了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之后,我们慢慢地就要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只意识到计划经济有毛病,觉得要搞市场调节。但那时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后经过对中外经验的反复思考和研究,逐渐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形成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念,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差不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了。这说明我这个人不很聪明,思想发展很慢,但我觉得这是符合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在“皈依”市场取向改革信念的同时,就提出不要迷信市场。我们应当重视价值规律,但不要认为价值规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去管。现在我还是这样想,不过是重复过去的观点,没有新鲜的东西,老一辈的人应该都知道的。
《经济观察报》:这就如同有人所说,您坚持认为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过时。是不是这样?
刘国光:从我上面讲的经过,你可以判断我有没有这个意思。既然“皈依”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既然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就是说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看待。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就不能再起作用了。至少在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都不能起作用,那是再也明显不过的道理。
不过,作为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前提下的“计划调节”(这里说的是广义计划,也包括战略性指导性计划,必要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等等),不能混为一谈。我在“答词”中说,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哪有作为制度的“计划经济”并没有过时的意思呢?!
我在提出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的时候,就讲了市场缺陷的问题。我列举了市场经济下不能完全交给价值规律或市场去管而必须由政府过问的事情。
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情是不能交给价值规律去管的。第一件事是经济总量的平衡——总需求、总供给的调控。如果这事完全让价值规律自发去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来回的周期震荡和频繁的经济危机。第二件事是大的结构调整问题,包括农业、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第一、二、三产业,消费与积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等大的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希望在短时期内如10年、20年、30年,以比较少的代价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现代化、高度化。通过市场自发配置人力、物力、资源不是不能实现结构调整,但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要经过多次大的反复、危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实现。我们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拖延的,也花不起沉重的代价。比如一些影响比例关系的重大工程规划必须由政府来做,反周期的重大投资活动要由政府规划,等等。第三件事是公平竞争问题。认为市场能够保证公平竞争,是一个神话,即使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可能保证公平竞争,因为市场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必然走向垄断,即不公平竞争。所以,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定反垄断法、保护公平竞争法等。第四件事是有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及“外部不经济”问题。所谓“外部不经济”,就是从企业内看是有利的,但在企业外看却破坏了生态平衡、资源等,造成水、空气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这种短期行为危害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生存。对这些问题,市场机制是无能力解决的。第五件事,社会公平问题。市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市场只能实现等价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平等精神,这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进步。但市场作用必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在我们引进市场机制过程中,这些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社会不安,影响了一些群体的积极性。对此,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种现象的恶性发展。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更不能少。
这些意见,后来我发现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阐述,所以我说的也不完全是新鲜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这也是您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我们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曾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您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笼子”还有必要?
刘国光:陈云同志讲得很生动。好像“笼子”这个词不好听,但要看到“笼子”的作用。国家财政预算把国家的收支大体框住了,是不是“笼子”?货币信贷总量调控把国民经济活动范围大体框住了,是不是“笼子”?重大的工程规划,是不是“笼子”?等等,等等。当然,这个“笼子”可大可小,可刚可柔,可用不同材料如钢材或塑料薄膜等制成,如指令性计划是刚性的,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总之,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忽视必要的“笼子”即政府管理和计划协调的作用。现在,“十一五”计划不说计划了,改称“规划”,但“规划”也是一种计划,只不过是长远计划,是战略性的计划和指导性的计划,不再是指令性的计划。它应该起导向作用,其中如重大工程项目的规划也有指令性的。必要的指令性计划也不能排除。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本身就包含着计划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计划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有效的政府管理。
我认为,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所谓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生着变化,通过政府的政策或计划的干预使市场经济不那么完全,不像19世纪那么典型。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场化的主张,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犯了错误,于是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分迷信市场,要重视国家计划协调、宏观管理与必要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弯路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对于当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经济学界与思想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关于腐败的根源问题,有学者认为,恰恰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才为“权贵”阶层提供了获得腐败寻租利益的必要条件与土壤,才有了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的恶果,如果市场经济更纯粹,行政计划就会消灭得更彻底,那么“权贵”们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捞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必定大大减少。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道理?
刘国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要分几个层次来讲。
一、你说问题出在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当然,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行政性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是不适宜的,会带来政府职能的越位,管了不该由政府管而应该由市场去管的事情。不过,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过小”,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过少”,也未必适宜,这会导致政府职能不到位,该当由政府来管的事情,它却推卸责任不管。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三位当事人(政府、企业、个人或家庭)之一和公众利益的代表,不能不掌握相当部分的社会资源,参与资源配置的活动,但其参与要适度,要尽量按照市场原则,同时必须考虑公共利益原则来做,这是没有疑义的。
二、腐败的发生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大,或者权力小,都可能发生腐败。只要法律制度和民主监督不健全,管不住政府官员的行为,就可能发生腐败。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大或者小,只影响腐败规模的大小,不是产生腐败的原因。根治腐败,要从健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入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才是治本之道。
三、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除了源于法治不健全、民主监督欠缺外,市场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温床。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不是计划经济固有的东西,而是我们市场改革以后才盛行起来的东西。过去计划经济并没有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这个东西。我不是替计划经济涂脂抹粉。过去计划经济有很多很多的弊病,搞得太死了,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官僚主义,也有权力的滥用,也有腐败,但是当时政府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极大,比现在大得多,而腐败的规模很小,只存在于计划经济的某些裂缝和边缘,更没有权力资本化市场化问题。权力资本化市场化问题,是到我们现在才严重起来。很难说这跟现在的市场环境没有关系。因为有市场才有资本,才有权力的资本化、市场化,没有市场,怎么搞权力的资本化、市场化?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不够,有点勉强,倒是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更为合理一些。而市场扭曲和市场缺陷,是市场化改革过程所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所以要强调政府来过问,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缺陷。
四、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计划与规划(这些都属于广义的计划),同某些官员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搞官商勾结、搞权力资本化市场化,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借口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为权贵阶层提供了获得腐败寻租利益的条件,来否定国家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与管理经济的职能(广义的计划)。前面说过,治理腐败和权力资本化、市场化要从逐步建立健全民主法治环境,从政治改革着手,现在还要加上,要从校正市场扭曲和纠正市场缺陷入手,这都少不了加强国家和政府管理或广义计划的作用。所以我在“答词”中说,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据我所知,许多读者都非常明白并且赞同“答词”中的观点,但是有些人硬要说我是回到计划经济,那只好由他们说吧。
《经济观察报》:您是说,您现在依然支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有人也指出过,您最近一直在主张“少讲市场经济”,是这样的吗?
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我在“答词”中说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生产效率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共同富裕的本质也就是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
请注意,我特别使用了“相对”这个词,是有精确的含义的。就是说,相对多不是绝对的多,相对少不是绝对的少。逻辑上不应混淆。
这些年社会主义也不是没讲,但是相对少了一点,因此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总体改善的同时,社会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向两极分化迈进,腐败和权力资本化迅速滋生,蔓延扩大。这种趋势是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因此,现在要多讲一点社会主义,这符合我国的改革方向和老百姓的心理。当然,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也要多讲。只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讲得越多越好。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接到很多读者的共鸣,很多令我很感动的理解。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触犯了我们的“改革人士”,说以后少讲市场经济“不行”。先生,我也说不行。但你为什么要曲解我的原意呢?当然,我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虽然注意了用词严密,但解释说明得不够,令人产生逻辑上的误会。幸亏人家给我“留有余地”,没有刚刚给我颁了奖就否定我的观点,我真不知如何表达谢意才好。
《经济观察报》:您在《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误导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有些人觉得您似乎是在主张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
刘国光:批评新自由主义就是“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吗?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吗?帽子大得很咧!西方新自由主义里面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有许多科学的成分,我们还需要借鉴,没有人批评这个东西。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我在那篇文章中列举了(如自私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自由市场万能论等)——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这样点评新自由主义怎么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倒退或者否定改革。我们经济学界许多同志批评新自由主义,大多是很认真的很结实的学术研究、学术评论,并不是一两句随便歪曲的话能轻易推倒的,要有有分量的学术论证。西方的正直的经济学人也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给前苏联、给拉丁美洲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我们的同志批评新自由主义,不是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担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改革决策是新自由主义设计的,目前它还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担心和忧虑这种影响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多余的。因为私利人、私有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等等,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渗透和流行,并且在发展。在上述文章中我曾指出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如果你赞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那是你自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现在有人自告奋勇承认自己接受新自由主义这些东西,又不准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批评了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倒退,就是反改革,哪有这个道理!
除了给批评新自由主义戴上否定改革的帽子,现在还时兴把这顶帽子乱扔,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反对改革的思潮。不容否认,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改革进程中出现了利益分化,少数人成为最富,有多数人获得一定利益,部分群众利益受到损害。人民群众和学术界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对改革进程中某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提出批评意见,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要把不同的看法说成是反改革。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西,发扬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不能把反思改革说成是反改革,你把那么些群众和代表他们的学者,说成是反改革的人,硬往反改革的方面推,后果将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愿意和努力使中国进步的人,要使得大家都来拥护改革。让大家都拥护改革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得改革对大家有利,就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此文经刘国光先生审阅、修改并同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