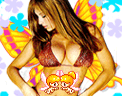学者称公众对经济学家不信任源自对现实不满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01日 14:47 南方周末 | |||||||||
|
本报11月17日刊载《我所了解的中国经济学家》一文之后,许多读者来电来函表达不同意见。同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和武汉大学经济学家邹恒甫的“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已从报纸、杂志、网络扩展到学堂乃至街头巷尾,在大多数人的话语里,“经济学家”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学界内部略带情绪性的评议何以引发学界之外的反应?学界内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评议?本报愿意为这次讨论提供一个平台,并尽可能客观地刊发多方观点,因此我们采访多位 □本报记者 余力 11月26日晚,在一位著名华人学者70寿辰的庆祝酒会上,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祝酒时说,“我看在座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就不止五位”,在座的数十名经济学者立即报以会心的掌声和笑容。 这是国内的经济学者们对当前争议的一次非正式回应,对他们而言,今年秋天有些寒冷。 自2004年8月掀起轩然大波的“郎顾之争”以来,为国企产权改革和市场化取向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成为备受指摘的对象——他们或被视为富人代言人,漠视穷人利益,或被指责过于关注效率,罔顾公平。 今年7月以来,随着顾雏军的入狱和医疗体系改革被一些机构宣告为失败,中国经济学家们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10月底以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和武汉大学经济学家邹恒甫分别对国内媒体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和“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评论,似乎为公众的不信任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他们都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或师从于国际一流学者,或学术成就已获承认。 在随后的一项媒体调查中,“5个论”得到83%的公众支持率。而中国经济学家们,则大多选择了缄默,多位学者在婉拒采访时承认,并非对当前争议无动于衷,但“不愿陷入论战漩涡”。 批评者已充分陈述,被批评者的主张也应为公众所知,有鉴于此,本报于近日分别约请6位经济学者,各自就他们感兴趣的争议发表见解,他们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香港大学副教授肖耿、西安交大教授郭誉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明干。 回应丁学良、邹恒甫 记者:如何看待丁学良教授所说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许小年:我相当程度上赞成丁学良的评价,确实有一些国内学者的水平比不上国外好的研究生院的学生。在中欧上课时,有学生问我如何看待这个提法,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成为第六个”。 史晋川:丁学良的领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他对于经济学家的评价,犹如没有专业味觉的食客评价厨师,至少不严谨。 谢明干:完全是无稽之谈。讨论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之前,起码要先给合格的经济学家下个定义吧。老一代的人,很尊重经济学家这个称号,至于我自己,到哪都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学爱好者而已。丁不是经济学界的人,怎么能随便发议论?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要的突破,经济学界都付出了心血,不能否认。 梁小民:如果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合格经济学家的标准,中国目前一个还没有。1个还是5个,显然无法证伪,因为没有标准。但确实,目前社会氛围浮躁,很难出大学问家,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缺憾,任何社会的转型时期都是如此——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在1930年代以前,又何曾出过大学问家? 肖耿:对于丁学良的说法我不感到吃惊,这是他的风格,但这样的评价与现实不符。一位前辈学者说,没有大批出色的物理学家,神六不会上天;没有大批优秀的生物学家,基因工程也就谈不上。然而,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破了人类历史纪录,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世行有8000多名经济学家(或分析人员),研究能力当然很强,但他们却对中国制定的经济政策非常钦佩和尊敬。 记者:邹恒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除了很少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之外,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主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国外,只有第三流的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一流的经济学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经济学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如何看待? 史晋川:这是很偏颇的说法。事实上,在国外排前20名的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中,50%以上是从现实问题的角度切入阐述理论的,这样或者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增强了解释能力、弥补原有理论的缺陷,或者发展出新理论。大量的国际一流经济学家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者。 当然经济学也有纯理论研究,如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但更多的是从现实问题切入的,或是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如经济学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后两类研究的成果已被公认。 肖耿:在世行时,邹教授的办公室在我楼上,他的表达个性色彩很强。中国需要纯理论研究,但也需要关于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在国外专业杂志发表文章作为评判经济学家的主要标准,这显然不妥:不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成名前难以在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中国一些人并没有经济学家的头衔,但他们具有很好的经济思想。显然,经济思想的高下才是真正的标准。 公众的不信任感源自现实问题 记者:去年“郎顾之争”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成为被抨击的对象,逐渐遭受信任危机,被质疑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及过分关注效率,不讲公平。这样整体性的质疑正常吗? 梁小民: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满,主要是对当前问题的不满。如腐败问题、贱卖国有资产、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最低层民众利益被忽略、下岗职工的隐性契约(原来的低工资包含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的支付承诺)没有充分兑现等等,公众中不满情绪在堆积,对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丧失信任,而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首当其冲。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着普遍的误解:经济学虽然是显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都能在经济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但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有限。 史晋川:主流经济学家是有经济学的定义的,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但公众理解的主流是指在政府经济决策咨询中较多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只是从事研究,并未参与决策咨询,指责他们是不公平的。 目前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更多地是质疑他们的动机,即他们通过为利益集团代言而获取利益,这是道德层面的指责。亚当·斯密曾说,人都是自利的。只要过程不违反法律,经济学家的自利并不是罪过。如果要求经济学家必须无私,那么也应该同样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否则就是将经济学家置于了一个泛道德化的要求下,基于这样的前提提出的指责毫无力量。 郭誉森:1960年代,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洋溢着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经济学研究已经找到了最后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可以从此摆脱经济周期的困扰。但1970年代随之而来的危机使学者们由虚幻的天堂坠下,公众对这个群体也有诸多质疑。我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经历了这个过程。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现在国内学者遭受的质疑并没有太让我感到惊讶,惟一的区别是像你们这样的全国性媒体可以用这么大的篇幅进行报道,在美国则不可能——没有那么多读者。 经济学家眼中的公平与效率 记者:在公众印象中,似乎主流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公平。钱颖一教授则说,“我们不是不关心公平,只是我们更关心如何以有效率的方式到达公平”,这样的表述如何理解? 许小年:中国自古代以来就有“均贫富”的公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以现代经济学解释,这样的公平是指结果的平等或收入的平等(equal income)。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观念需要改变:市场经济强调以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的后果是优胜劣汰,结果的平等难以实现。 市场经济学中的公平概念指机会的平等(equal opportunity),这样的公平概念与效率没有冲突。如开放垄断领域,既实现机会的平等,又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而政府官员通过手中权力寻租,就是典型的机会不平等,既不公平,也无效率。 不能把存在问题归咎改革 记者:目前经济学家遭遇的信任危机,能否单一地来看待它? 谢明干:现在有一些观点,把许多问题归咎改革。 20多年的改革道路并不平坦,对改革的看法有多次争论和反复。我已70多岁,记忆中此前大的争论有两次。 最早一次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争论的焦点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争论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写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告终,我当时在中央经济委员会工作,参与起草了决议。决议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突破,给改革很大的推动力,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反对改革的思潮,特别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很多,第二次争论,一直持续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 1991年-1992年中,理论界十分混乱,改革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被点名批评。小平凭借他的政治智慧,果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平息这次争论。 此后十年的时间相对平静一些。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继续深化。 但对改革的怀疑从未消失过。其实,争论的中心,无非就是计划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有一两百年,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样的争论。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到新自由主义,争论本质一样,但实际内容有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时起时伏。这种争论并不奇怪,我想以后还会持续,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地论证哪种手段对、政府干预究竟要不要、政府要干预多少。 新自由主义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西方国家给拉丁美洲复兴开出的药方,叫《华盛顿共识》,根据西方经济发展,归纳出十条,如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的管制监督、加强调控监督,等等。一些国家视之为圣经 ,WTO、世界银行等,也通过贷款将这些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拉美一些国家强调自由化,引起经济倒退,GDP下降,他们在总结经验,抛弃了华盛顿共识,反而转向中国的经济,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家。 我们的经济发展 ,与西方肯定不一样。我们的改革一直是处在政府领导下的 ,不能与拉丁美洲的情况混为一谈。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很多问题、治安、贫穷、腐败等等,都是改革造成的,以此抨击改革。 的确,改革以前,不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什么都没有,腐败不起来。改革就是为了搞好生活,发展道路上有贫富差距,这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均匀、不和谐,但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怎么能把暂时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归到改革的头上? 目前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对经济学家整体的批评,是整个争论的一部分。面对新的否定改革的思潮,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我们的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人民的实践,汇集经济学界的智慧,慎重地出台政策。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改革是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模式。国外说的中国模式—— 就是一步步地、渐进地,按照中国国情,考虑到社会的接受能力,考虑到保持大局稳定,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推行我们的改革。 今天的世界经济,没有哪个国家有绝对的自由经济——政府毫不干预,绝对完全的自由主义。即使是香港这个最自由的地方,也需要干预,否则社会会乱。 美、法、日、德、瑞典,等等,他们同样也需要政府干预。他们的社会保险做得很好,很厉害,都是政府在后面支撑。社会发展到今天,没有学理上的自由主义,只是干预的多少、时间问题。 不能把我们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扣到改革的头上。不改革,大家都很穷,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才改革。有问题,就要改革,解决问题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问题,但也不能由此从根本上来否定改革。存在问题,但不能夸大,真实存在,要客观、正确认识它,才能解决。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12月大黑马免费送!!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美国保佳教您赚百万! |
| 完美女人是怎样炼成的 |
| 开男士品牌名店赚疯了 |
| 名品服饰 一折供货 |
| 关注:肾病、尿毒症!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瑜珈美容俱乐部太赚钱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开个咖啡店赚了几百万 |
| 拯救男人,还你健康! |
| 中国1000个赚钱好项目 |
| 让男人更自信的武器!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