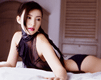|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推动经济增长最终还要货币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李冰 发自北京
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除了要考虑GDP的平稳增长外,投资和消费的平稳增长以及相互间的均衡同样非常重要。但对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机制的复杂性使得投资和消
费均衡的调控,具有一些不确定性。
日前,就中国当前宏观调控下经济增长中的投资与消费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正处于转轨和经济增长时期,目前,中国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具有哪些特殊性?
刘伟: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投资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改革开放26年的经验表明,固定资产需求投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3.5%左右。当投资总量增长率波动范围在3.5%到23.5%之间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大体承受,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后果。消费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增长的波动幅度大大小于投资增长波动。
《第一财经日报》:为达到投资和消费的均衡,我们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和顺序,投资和消费的调控目标分别怎样协调?
刘伟:应当遵循投资的增长略高于GDP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9%的领域里,大约高4个百分点左右;而消费的增长略低于GDP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9%的领域里,大约低1%左右。
但中国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量具有机制的复杂性,既不完全是计划经济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机制下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所以,常常是宏观政策的作用,反而不如一些微观手段的作用大。
《第一财经日报》:机制的复杂性对于宏观调控的结果造成了什么具体影响?
刘伟:本轮宏观调控强调结构的调整,对不同行业、企业、地区之间采取了区别对待。这种方法起到了作用,但有的区别对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的独立性,更多是依靠行政手段。
另外,这次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府行为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这与26年来的机制变化及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府权力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是靠招商引资,这种招商引资地方政府要在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付出代价。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越来越倾向于财政收入最大化,所以,地方政府目标与中央政府目标就会产生偏差。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说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的深入,但对中央如何协调好调控与地方利益的关系,以及达到投资与消费的均衡带来了不确定性。
《第一财经日报》:您前面提到的微观手段的重要作用是如何表现的?
刘伟:此次调控中清理土地的微观手段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固定资产投资过热迅速见效而降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通过土地的清理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抑制,之所以起到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因还表明,目前中国要素资源的配置还是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要素还掌握在行政手中,要素的配置并不是以市场为主。这种手段可以采取,但不宜长期采用,长期还是应该以市场为主,以市场手段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
《第一财经日报》:这一轮的调控中,政府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收到了实际效果?
刘伟: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更为突出,这给人造成错觉,认为在调控中扩张性政策靠财政,紧缩性政策靠货币。财政政策只起到一个导向作用,要拉动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货币政策的支持。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相吻合,限制了社会资本的投资,也降低了社会总需求,同时对社会资本的正常投资不公平。但目前采用这种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还是很大。插图/苏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