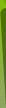秦晖访谈:什么是我们的真问题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26日 20:31 人物周刊 | |||||||||
|
现在学界的一个问题是,大量存在的学术泡沫,本来3000字能说清的,100万字说得你糊里糊涂。原因之一就是无视常识 国企是谁的?当然是国民的,这有什么可说的? -本刊记者 刘天时
1月11日下午,秦晖教授坐在家中客厅沙发旁边的矮凳上,身体前倾,一件土黄色棉布外套规规矩矩,小翻领领口露出的毛衣秋衣,层层叠叠,灰灰秃秃。在他的周围,这个百来平米的单元房,门厅一张刨花板面的折叠饭桌,屋内直抵天棚排满四壁的书架——有列宁全集,有女儿的照片,有会议纪念的工艺品……俗常、拥挤,不怎么个性光鲜。 而此前,在各种场合遇见过的秦晖先生,也是很容易被说成“本土”(或者“土”)的样子:酱色的塑料框眼镜,暗色的衬衫,下摆散着,坐在沙发边边上;发言也没有“抢”啊“驳”啊的风头,但一说就又说开了,不瞻前不顾后地,往细往远了掰扯。 这一天,从3点到6点,他是一直在讲话的。虽然感冒还没完全好,喉咙和鼻子还在消极怠工。 在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话里面,有很靓丽很时兴的词,比如自由、民主、公正;也有些拗口的句子,比如,“一个假说被证伪,一个更完善的假说被证伪……不断证伪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但最终也没法达到真理的过程”,再比如,“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大是原因”;有近在眼前的现实,比如“下岗”、“医保”,有远在天边的学理,比如“罗马法”、“嘉兴藏”;……像是急切的喃喃自语,散漫里有焦灼;像是游离的广场演说,切实里又有超脱。 而此前,对秦晖先生著说的阅读经验,除了“思想和理论”的学习,也补充证实着这样的感性印象:这是位对枯燥的渊博知识、拗口的繁复道理,在行又享受的先生!人格修养上的谦卑掩映着智力上的优越;义愤害臊地躲在与价值无涉的逻辑链后面;责任心呢,又要固执地站到学术研讨前面来;…… 关于 “心历路程”,秦晖先生青少时代以来的回忆提供了这样一些镜头: 之一,1969年的南宁,省图书馆,少年秦晖,一边神色严峻地飞快翻阅,一边如获至宝地唰唰摘抄。时而眉头紧锁,时而豁然开朗。这安静空荡荡的书库外面,是一个时代的嘈杂和浮尘。 之后不久,秦晖揣着一颗15岁的赤诚之心以及一书包“如何又快又多地灭田鼠”、“如何用辣椒制作土农药杀蚜虫”的资料卡片,斗志昂扬地来到广西百色田林一个离县城100公里的村子,准备大干一场——当然,幸好没什么实践机会,这些浮夸时期出版物提供的“土洋结合”的农技知识,也就没造成什么祸害。 之二,70年代初的广西乡下,秦晖在种田,在劳动的间隙,坐在田埂上,他准备与老乡们“打成一片”悉心听取人民群众的心声;可是他听到的心声,基本是张家长李家短,是黄段子是无厘头……于是只能面红耳赤只能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 “当然这不会使我‘看不起’农民,因为意识形态教育使那时的我相信这些都是‘支流’、是‘表面’,当老乡和我谈起生产或者队里的公事时我会找到对‘贫下中农’‘本质’的感觉,更不用说假如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些什么忆苦思甜忠党爱国为革命种田的大道理——可惜这类‘本质’话语我从未听到过,除了开会以外。遗憾的是老乡们——其实我也一样——总是生活在‘表面’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中。” 之三,还是贫穷中国荒唐年代黯淡寂寞的小小村庄。秦晖在自学,农机、水电、医药。他钻到拖拉机下面在修理发动机,他指指点点在修建社里的第一个水电站,他在给老乡们开药方……因为学农机学水电学医药,他又学上了电学、三角、植物分类学,因为要尽量多地参阅资料,他又学上了英文,用拼音标注的又聋又哑的顶呱呱的英文。 “那时候的学习基本是求智爱真型的。虽然学了很多实用之学,但那些年里,农村技术‘职位’也是计划体制下按‘关系’分配的‘稀缺资源’,并不是具备有关知识者就可以此‘谋生’的。因此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主要还是‘务虚’,是为了免于精神饥渴;低调点说,是为求知而求知,高调点说,是为追求真理——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调,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真理’,你还能追求什么?” 之四,又是图书馆,这回是县图书馆;又是如饥似渴,却是不红也不专的、“文革异端思想之源”的“灰皮书”,60年代为反苏翻译内部发行分级选阅的书。这时候的秦晖,20来岁,不时被借调到县文化局搞民间文艺创作,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于是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这之后,在乡下锻炼了9年之后的1978年,投考中国农民史学开创人赵俪生先生的研究生,做学生做教授,从广西壮乡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从农民战争农民农村问题到经济史到转轨比较,从先秦到明清到当代,从“自我陶醉地”做考据派的“死学问”,到为“现实的问题与主义”,“据常识守底线”、“不得不发言、不得不辩论”……秦晖,这位先生,他的视界和声音,“自然而然地”拓宽、“顺理成章地”搅深。 “涉猎广、专业领域淡化、逆潮流而动,但始终是有社会关怀导向的。20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 “关怀”、“责任”,在秦晖先生这里,又低调又骄傲,似乎也不大有深沉而光辉的扮相。比如,当你继续追问: 追求“真善美”的童年期表现? ——求知欲本身是没什么目的的。说好听叫忧国忧民,其实就是纳闷。我并没想当什么家,只是拿到一本书,就很高兴,就很喜欢看,而且这兴趣是不断转移的,比如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天文学,有段时间还做过发电机、电动机。 能回忆起来的最早的理想? ——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不提倡个人理想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甘当革命螺丝钉”。当时是很忌讳说当这当那的。而且我们真的也没想,真的没什么雄心壮志。 最早有公民概念是什么时候? ——潜移默化吧。“文革”时不也讲“天下我们的天下,国家我们的国家”吗?那时候人们还是很虚假地认为有责任感的。 内心会激荡不安吗?为大的问题,比如公正民主自由…… ——有。我关心的事情都是和“我”有关的,不仅仅是我研究的课题,我本身也是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主体啊。 焦虑或者愤世嫉俗吗? ——这种情绪一直都是有的,就是不满意呗,就是想求变求新。人之常情。 您是乐观的吗? ——沮丧无奈,任何时候都会有的。但我是信仰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的。中国现在的事情办糟了,直接责任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再往前,顶多能往前追到上一两代人,你再把它追到孔夫子啊秦始皇啊,就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是可以从数学上证明的。绝对的乐观或悲观,都没什么根据。对公共生活的关注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有正常智力的公民都有这个判断能力。 …… 在天命之年,秦晖先生,在内心,在书斋,在晴冷的冬天北京,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在交替的澎湃和安静之间,一如既往地,自得其乐地,做着他所谓的“底线之上”的思想实践——“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 从历史转入现实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产权改革一直是媒体报道和学界讨论的热点,您在其中的发言也比较频繁独到。您也谈到,您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关心“分家问题”了;而在十几年前,您为人所知是因为您在农民史问题上的研究。您最初关注转轨是出于什么契机呢?是接待了某个上访者,还是出于对政策研究的直觉,或者别的? 80年代我做的学问主要是农民史。我们把农民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但也关心现实的农村。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过去的一些论说有很多不能成立的地方,比如把传统农村基本矛盾理解为租佃矛盾,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作解释工具;而我们试图以比较的视角,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维度,所以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比较经济史、现代化研究,也是我们用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不过那时侯的很多感想,基本还是以历史研究著作来反映,不直接谈现实问题。 后来,80年代末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历史和现实是打通的,历史并没有真正过去,我们也一直生活在历史之中。正因为研究历史,所以看待现实问题时才会有纵深感。比如,那段时间,有很多人认为,改革会中断会趋于保守;但事实上,政治上是如此,但是在经济改革上,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加速了。我一直就有这样的预计,因为,道理很简单:在没发生冲突之前,旧体制还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大家长摆出慈祥面孔,子弟还要表现孝顺,虽然大家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但面纱被挑破了,大家都看透了,家长不能指望子弟孝顺,子弟不能指望家长慈爱了。再加上,那时候,很多利益群体不能说话了,强势利益群体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搞,一些改革就更容易了。 而且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比如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似乎是保守派镇压了自由派,但反过来,保守派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比自由派更自由。 凡是在这种背景下的改革都有共性:都是强势阶层推动的,缺少公共参与的空间,缺少讨价还价的机制,基本上是以强权为杠杆,以既得利益为动力的。从方向上讲,是进步的趋势,但是手段缺乏公正性,在正义和道德合法性上缺失,而且会造成后遗症。 想知道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您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曾经为很细节的东西,多次去云南;现在的产权改革研究呢?实地考察民间访谈多吗? 从国内史学界讲,我是最早运用基层档案做现当代研究的。1980年代,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老师,搞函授,跑了很多县档案馆,那时候是没对外开放的。档案中有活的历史,比如土改一段,我根据档案的线索,找到了当事人做访谈。后来到了北京,参与组织了一些农村调查,并与改革机构有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另外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实感就更多了。 在研究方法上,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普遍的问题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脱节,要宏就一直宏下去,要微就一路微下去,两者不能形成认识循环。我想更好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宏观研究从认识论上,应该提出具有明显的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因为边界清晰,或者可以证实或者可以证伪,形成启示,引向微观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宏观含含糊糊,大而无当,看似什么都能解释,实际上什么都解释不了。我觉得应该是,宏观理论促使微观研究,微观研究对宏观理论研究证伪,然后产生第二代的理论,从而形成知识的循环。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遵循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赵俪生先生的教诲,按他的说法是: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既要避免宋学传统的空疏,又要避免汉学传统的豆丁。 您在做企业转制研究时,与企业工人、管理层的实际接触,对您的研究重要吗?会有上访的人向您求助吗?有哪些技术帮助您把握案例研究中的客观性? 会有接触。我讲的问题,基本都是有经验基础的,但一般不直接介入案例,那样会陷入是非。我的研究是,把案例归纳为问题,进而理论论述。其功能,在于提醒相关的注意,注意存在的问题,具体解决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在采集事实时,会尽量从各个不同角度。而且我也相信: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能标榜自己绝对客观,但是在主观上要有追求客观的愿望。只要有这个愿望,看问题即使是有价值取向也问题不大,因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互补。任何人类知识的增长,都是通过深刻的片面性互相补充完成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探讨问题的机制和环境。 整天收到类似的来信,多极了。但我的身份其实只是学者。 中国人缺少逻辑能力? 可能因为您的观点,您一贯的姿态——强调改革的公正公平,申张弱势群体的权益,让大家对您的影响力的期待,不仅仅限于一个学者…… 作为学者,我并不认为我主观上有很强的为某一个群体说话的冲动。我不是政党领袖,也不需要争取选民,所以没这个动机。我写,当然是有我的价值关怀在里面;但我还是试图逻辑严谨、有事实根据。但是,还是有冲动的,还是有感而发的——在有据而论的基础上。 至于影响力,我想是,尽人事,由天命。这个应该不是我主要考虑的东西。我既不是冷漠的,也不是单纯地喜好感情宣泄。我做的事情,什么性质,很难说。什么是学术呢?我想,第一是有实证基础的,不是创作;第二,在实证基础上形成思想,逻辑上是严谨的,带来知识增量,扩充人们的认知领域。现在学界的一个问题是,大量存在的学术泡沫,本来3000字说能清的,100万字说得你糊里糊涂。原因之一就是无视常识。 “常识”也是您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您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在常识之上思想》。您确实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现实中吗? 有些很简单的问题是被复杂的语言说乱套的。比如,国企是谁的?当然是国民的,这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有人就说了,国企本来就不是大家的,国企是法人的,似乎法人可以是脱离自然人存在的一样——其实人所共知,法人背后是必然有自然人作基础的;还有人说国企是无主物,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私拿了,就会被认为是贪污,如果是无主物,按罗马法,发现者所有,是非常正当的;还有人说国企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就可以给私人吗?逻辑上说不通啊;还有说,本来就是抢的不义之财,现在就要还给资本家,但如果是不义之财,就应该还给“那个”资本家,而不是抽象的资本家阶层,你如果从甲抢来的东西还给乙,那是双重的不公正。 反过来说,因为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而否定国企改革的人,也违背常识和逻辑。比如说,郎咸平说,谁能证明国企比私企没效率,你给我拿出数字来。这还用拿数字吗?既然你在那大声说国资流失,既然国企连照料资产都做不好,还怎么谈更有效率呢?而且我们说有无效率,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但国企,很多都是垄断,垄断就谈不上有无效率。 那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没有逻辑”?是智力、或者中西文化上的什么差异吗? 不能这么说,并非中国人就缺少逻辑能力,很多情况是背后有太多的利益推动,有意忽略罢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在用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成本的降低”为用专制手段私自处置公共资产的行为辩解,说,不允许各阶层谈判、掌权人任意处置,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作为事实,是有的,但合理性何在啊?这和科斯(注:交易理论提出者)讲的是两回事,他说的是企业节约交易费用,他没说强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也从来没认为可以通过剥夺人们交易权利的方式降低交易费用,科斯的节约交易费用,是在人人有充分交易权利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按照这种强盗逻辑,奴隶制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因为我把你的交易权利剥夺了,你就不交易了,那不就最省了吗?比如古拉格群岛,那还真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 您的文章中经常会提到这个是“假问题”、那个是“伪命题”,您似乎费很大力气在做澄清工作。 是啊。比如在东西问题上,我就觉得有一种偏向就过了,就一直在回避真问题。这个偏向过分强调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好像西方人和中国人有什么天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好像西方人就更爱自由,而东方人就喜欢有一个大家长管自己。哪有这回事?那为什么外国的监狱中国的监狱都要上锁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自己原来也有似是而非的时期,也写过,“中国人害怕风险,西方人爱好冒险”之类的文章。但我现在觉得,中西差异的真正所在是,人们面临的现实的问题有很大差异,中西交流的隔阂,并不在文化。 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关于目前中国需要左派还是右派,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学界争论得很热闹,而您似乎对这两方都有不满不屑,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假问题。 就本意而言,自由主义是关于限制政府权利的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关于强化政府责任的主义,本来是不相冲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从来不会直接讲政府不负责任,民主主义从来不讲政府可以为所欲为权利不受制约;但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在宪政框架下是统一的,你讲责任大,你就得承认他的权利大,你讲权利小,你就得承认他的责任也小点。所以就形成对立了。因为作为统治者,当然是想权利大责任小,为所欲为,想抢什么抢什么,同时对你的死活不闻不问;对老百姓讲,正好反过来,一方面希望权利意义上的小政府,尽可能的多自由,又希望是责任意义上的大政府,尽可能的多福利。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所以宪政解决的就是这个责权对应的问题。 但在此、在宪政之前,你完全可能面对一个责任小权利大的政府,那么你面对这样的政府,你可以同时要求,一方面限制政府权利,一方面追问政府责任。也就不存在大小政府的争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自由多些还是福利多些,就现在的中国,当然是假问题。真问题的双方是这样构成的:以“限制政府权利扩大责任”为一方,以“推卸政府责任扩大政府权利”为另一方,我们要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和分野。这是“是否要追求一个责权对应的政府”的问题;是“是否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民主权利”的问题;是否坚持底线的问题。 既然您近年来研究国企转轨问题,能否就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情况下,排除政治因素的阶级分析不大可能。中国的现实是,单位不同,同样是工人,状况可能很不一样;企业家也是,有权力的和被权力勒索的,处境很不同。但中国目前,在现阶段改革过程中,无权势者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秦晖底线 秦晖曾多次针对国内学界“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断然指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我们应该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共同追求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赞同的基本价值,比如基本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这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 秦晖思想关键词 关于产权改革 卖方缺位 一项资产面临处置,但是没有来出卖的人,也即所有者缺位。 看守者交易 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政府只是看守这些资产。政府却利用权力对其进行处置。 界定式私有化 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由于国有资本存量太大难以卖掉,就干脆采用划拨方式径自将其从“国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 经营者持大股 在股本设置时,向经营层倾斜,鼓励企业经营层多持股、持大股,避免平均持股;鼓励企业法人代表多渠道筹资买断企业法人股,资金不足者,允许分期付清(亦即可以以未来红利冲抵)。在以个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允许将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优先划转到企业经营层个人的名下,实行贷款转股本,引导贷款扩股向企业经营层集中。 内部人私有化 以长沙湘江涂料为例。只把17年前的或企业创建时的初始投资算作国有,而以这些投资为本滚动产生的“积累”都被“界定”为内部人(“企业集体”)资产。这样“界定”,80%的企业资产便从“国有”帐上消失并转入内部人手中,再经“优惠”赎买,余下的20%国有资产比率又缩水成了6%,连同未进入新企业资本帐内而是上交财政的赎买金,共为12%,亦即88%的原来人们心目中的国有资产“在10天左右时间里”都被大笔一挥“界定”掉了。 关于中国道路 中国原始积累的方式 中国权贵资本在一开始民间经济贫瘠的情况下,主要靠的是从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为公”,另一方面“化公为(权贵之)私”。 中国可能面临的危险 历史上反民主的寡头主义与反自由的民粹主义往往互为因果,造成“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之恶性循环。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风险。 中国应该走的道路 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 秦晖 生于1953年,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编委。 1980年代初主要研究农民史,后期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近年开始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关注国企转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弱势者权益受侵害的问题。 主要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市场的昨天与今大: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实践自由》等。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经济学人--秦晖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