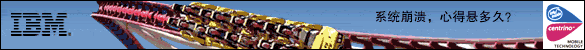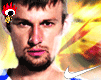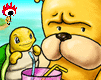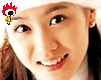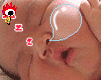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在历史的边缘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1日 14:20 中评网 汪丁丁 | |||||||||
|
汪丁丁 “上帝死了,人被遗忘了,历史终结了。”这是眼下流行的也是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三位一体’命题。1889年1月一个阴暗的下午,写下“上帝死了”的尼采大约是最后一次在土伦街道上散步,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几分钟以后,他紧紧搂住一匹马的脖子,瘫倒在地上。疯子尼采在本世纪第一个八月份死去了,这是一个征兆,此后的一百年,整个西方社会陷入
历史终结了。但那只是西方历史的终结,只是基督教历史的终结。或许,世界历史将随着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历史的终结而终结?不论如何,人类历史肯定经历过不少次类似的‘终结’,我把这叫做‘历史的边缘’。这是‘时间’意义上的‘边缘’。其次,我们必须明白,在这部以西方为主的现代史里,中国处于边缘。这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缘’。最后,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对‘主流生活方式’保持批判的态度,这是让社会获得健全精神生活的几乎唯一的方式。这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缘’。在这三重意义上,我们守候着历史的边缘。 未来的一千年,什么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人类发展?在我能够展开这个问题之前,我应当说明: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它正受到环境主义者广泛和深刻的批判。而环境主义的自然哲学观念在根本上是与东方思想相通的。也就是说,植根于两千年前古代希腊思想的‘发展(genesis)问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东方的永恒的静止的善。这永恒的宁静曾经被埃及的祭司们写在<死人书>里面,并且以谷神和酒神崇拜的方式将希腊哲学及此后两千年西方精神的潜意识,统统笼罩在迪奥尼索斯的疯狂之中。叔本华和容格,先后意识到西方精神的潜意识疯狂必须从东方的安逸自足的精神里寻求解脱,才可能使心灵恢复“如瑞士湖泊那样清澈与宁静”的状态。因此,按照希腊悲剧的思路,在未来的一千年里,经历了两千年自我放逐的西方精神,这个代表着人类命运的俄迪普斯,将返回它在东方的家园,在那里他将再次面对斯芬克斯---东方的真正的斯芬克斯。 所以,当我们询问‘发展’问题的时候,这问题本身总是反过来提醒我们:任何发展问题都首先是精神的发展问题,其次才是物质方面的发展问题。后者只是前者的结果。当精神愿意把它已经意识到了的世界付诸实施时,它便展现为物质的世界。 在‘一千年’这样一个时间视角下,日常的,短期的冲突早已被时间淹没。那些可能在一千年的时段上突显出来的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那些足以被‘年鉴派’历史学家称为‘长期因素’的结构性变量,在我看来只有两个:(1)资源与环境。这一概念最狭义的描述是“不可再生性资源”(矿产及其储量),而它的广义描述则包括了‘环境’本身;(2)技术与知识演变。这是不同的两件事请,前者是‘人对自然’的单向关系,后者则包括了关于‘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对人’的关系。就单纯的‘人对自然’关系而言,‘技术’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过程,从而有所谓‘进步’。但就复杂的‘人对自然’同时‘自然对人’的关系而言,‘技术’不应当再意味着对自然的征服过程,而应当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同一化过程,所以我用了‘演变’这个更为广义的表述。 关于‘不可再生性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的标题下已经谈论了几十年(至少从1970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开始),但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仍然没有碰到‘发展的极限’。每一个‘极限’设定都不能不假设一个有限的给定的资源储备总量,否则就谈不上‘发展的极限’了。可是当我们试图界定‘资源储备总量’时候,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一变量不能不依赖于人类知识的演变。如果没有充分发展了的化学知识从而‘石油’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人类就只能谈论以‘煤’为主的能源储备。能源如此,其它一切‘资源’亦如此,因为‘资源’是‘技术’的一种类型,而‘技术’是‘知识’的一种类型。知识演变决定‘可利用资源’的意义及储量。 假定一个合理的长期的资源供给增长速度,经济学家便可以谈论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例如根据索罗增长模型我们能够简单地推算,在足够长的时段内,人口的增长速度(稳态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零)和储蓄率(对应于稳态人口的储蓄率是零)都可以被忽略,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将唯一地取决于技术进步速度。在物理学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经济增长视为‘能量-效用’转换过程,而技术则决定了这一过程的转换效率。如果效用函数的结构参数保持不变,那么,索罗模型意味着:以百分比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能量供给的增长速度加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速度唯一地依赖于人类知识演变(‘资源储备总量’与‘技术’)的速度。但是这仍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的命题,因为它没有考虑上述增长方程里‘效用’的度量及其变化,而任何‘增长’都必须是在‘效用’增长的意义上成其为‘增长’。 什么是‘效用(utility)’?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个不能提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切经济学问题的前提,它的基础不在经济学领域内。‘效用’,当它被边沁从休谟那里拿来并大大推广开来的时候,它始终就是一个道德哲学概念,用边沁的话说,就是“对幸福程度的衡量”。而‘幸福(happiness)’,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与另外两个概念---‘卓越(excellency)’和‘善(good)’,一起构成了西方人所理解的‘伦理(ethic)’或‘道德(morality)’的主题。不是巧合,经济学家所说的‘物品(good)’---那个增加‘效用’的物品,正是道德哲学家所说的‘善’---那个与邪恶相对立的善。因为对西方精神而言,个人幸福,善,卓越,这三者原本是一回事。这里,我愿意宣称:使西方精神最终大大地不同于它所源出的东方精神的那一关键环节是‘自我(ego)’意识的独立化。注意,我用了狭义的‘自我’概念---‘ego’,而不是英文通常使用的广义的‘自我’概念---‘self’。后者不仅包含着前者,而且还包含着前者的对立物---潜意识。正是由于西方精神的‘自我’意识从‘集体’意识当中独立出来并且将‘集体意识’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去,才产生了具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幸福,自我的善,自我的卓越。这组‘三位一体’的价值是通过自我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来实现的。 假如有一天人类精神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变,从追求自我幸福转向追求‘超越自我’的幸福,那么显然,‘效用’,作为‘幸福’程度的度量,它的增长方式也将发生方向性的转变。例如,不难想象,一位精进的瑜伽师所体验到的‘效用’可以在能量投入完全不增长(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随着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断增加。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技术’或知识的演变,而是精神取向的转型。 综上所述,我可以把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抽象地概括为“由人类知识演变和精神取向决定的效用增长过程”。在这样的概括下,我们注意到‘效用增长过程’的意思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没有指明是谁的效用在增长。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不解答这类问题,因为这是有关‘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效率’的问题。而且,就长期增长而言,那些没有能力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制度迟早会在制度竞争中消亡,所以长期生存下来的经济制度必定是已经不存在分配问题的制度。换句话说,就‘长期’而言,不存在一部分人效用增长长期超过另一部分人效用增长的可能。这样,长期效用增长就有了明确的意思---每一个人的效用的长期增长。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如上所定义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的次一层的问题,或者说,那些在更短的时期内---例如三百年内---可以显现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类问题有两个:(1)人口结构变迁,人口年龄结构从初始态过渡到稳态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三百年。长期人口过程的常态可以用稳态年龄结构来近似,因为医学知识的积累不足以无限制地提高人类的期望寿命,未来二百年内,如果基因技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世界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很可能仍然停留在百岁以下,这便给出了未来人口稳态年龄结构的主要前提(假设由制度提供的激励使得人类生育率稳定在‘替代水平’上);(2)文化与制度变迁,这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它们可以被视为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文化是行为规范的无形部分,制度是行为规范的有形部分。文化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持续积累的非稳态过程,这里涉及到两个互相补充的特征:(a)积累---任何变化都是积累的结果,突变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才有了‘传统’;(b)非稳态---变化持续地发生,所以才不断地‘积累’,也因此而有了‘传统的转化’。 基于这两个‘结构’,我们便不难想象一个社会如何把给定的能量转换为特定的精神取向指导下的效用。尽管上面的分析表明:在这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例如制度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在几百年的时段上假设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稳定的和可以分离的。这样,主要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供给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主要由文化与制度变迁决定的消费需求和需求结构,这二者大致决定未来总供求的均衡。然后,由未来的均衡总量与目前均衡总量之间的差,可以推算出长期经济增长的平均速率。与那种简单地从目前经济与人口结构按照适当猜测的百分比外推的预测方法相比,我在这里描述的方法显然有更扎实的理论根据,虽然,它不如前者‘好用’。对于如此‘长期’的展望来说(如果‘预测’是不可能的话),我宁可更相信理论而不相信根据目前水平简单地外推。不论如何,让我给出简单外推得到的两个极端结果:(1)根据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以3000美元为例),假设年均实际增长1%,外推到2500年,将达到人均收入434000美元(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假设年均实际增长0.1%,其它条件不变,那么2500年人均收入将达到5000美元。我觉得我们大致可以在这两个数字所提供的巨大空间里发挥我们关于未来一千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想象力。同时,这样一种长期的历史视角也为更近期的预测提供了理论(可能的)范围,使我们的近期展望不至于太离谱。 在更短的时段上,例如未来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前景如何呢?在这一时间层次上显现出来的因素,我觉得有两个:(1)权力结构,这是一个(至少在福柯的大量论述之后)变得非常宽泛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指人们(包括人群与国家)在制定经济博弈的规则(包括国际规则)时相互之间的影响力(例如‘市场权力’,‘政治权力’,‘话语权力’,...)。权力在不同人群及同一人群内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显然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效率(华伦斯坦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对边缘关系”的论述是对不同人群之间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批判;制度经济学则论述了权力在人群之内不平等分配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2)政治经济体制的转换方向。如我始终强调的,中国以及整个非西方世界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被与之激烈竞争着的西方强势文明带进了一个千年未有的‘转型期’,我不知道这一转型期会在未来多少年内结束,但由于它涉及到我们已有的传统向着‘现代’的转化,如上所述,这一文化变迁达到稳态所需的时间不会少于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2100年以前将始终处于‘转型期’。与此相应的是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未来的某个相对稳定状态的过渡。‘相对稳定’,是因为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是持续的和非稳态的,所以把‘转型期’与其它时段区分开来的,只是变动的相对速率。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效率及其效用的增长取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方向。按照以往的经验,市场方向的演变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的不合理安排从而降低了经济的效用。 就长期而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才刚刚开始。虽然这一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之一,从而与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一样悠久,但它真正统治世界是在1990年代以后,当遏制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主要力量---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时候。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贸易,专业化与规模效益,而经济一体化所要求的‘统一规则’是在贸易伙伴们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100年内),这一权力格局将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从而基于这一权力格局的经济博弈规则将在西方价值观念的主导下形成。如同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曾经和仍在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附加效用(所谓‘铸币税’)一样,西方价值观念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规则也将为西方带来巨大的附加效用(所谓‘权力租’),这一附加效用是如此巨大以致华伦斯坦干脆认为整个‘第三世界’只不过是在为资本主义核心地区输送资源而已。但是公允地说,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欧洲社会的特殊形态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例如它所创造的科学与技术),尽管它的权力格局使得更多的好处被送往它的‘核心地区’。 未来一百年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源自欧洲社会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特殊形态是否有内在条件和外在可能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秩序?扩展秩序思想的创始人哈耶克反复表述过,任何扩展秩序都必须与本土的传统相适应,否则就无法成为‘自发的’扩展秩序。那些从外部强加给本土社会的合作秩序,哈耶克指出,将如古代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与瓦解那样迅速垮台。我一直将哈耶克的这一思想视为是对当代西方霸权意识的警告。因此,未来世界的经济秩序能否承担人类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非西方社会里实现‘本土化’。而西方规则的本土化将取决于两个因素:(a)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权力格局是否足够尊重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与价值从而愿意修改规则以容纳本土知识(这意味着放弃一部分‘权力租’);(b)非西方社会的本土文化是否有能力适应这一西方主导的扩展秩序的博弈规则(这意味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我看来,在这一趋势面前一切非西方社会的命运不外三种:(a)融入西方社会,放弃本土传统,所谓‘同化’。这一现象既然以前发生过多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以后不会发生;(b)自居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外并承受相应的后果。这也是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现象,事实上,人类几十万年的社会生活只是偶然地在几百年里被商业民族的活动连接为一体;(c)以精神力量修正西方制度,形成普遍主义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对此没有太大信心,尽管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也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非西方社会的这三种可能的命运也就是它们未来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三个可能的方向,而这些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大致上就决定了权力格局及其演变方向。例如,在某个时期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社会正在(似乎)被西方‘同化’(上述的命运(a)),于是相应地,我们会意识到权力格局的重心是西方力量主导的---如果存在一种社会心理度量,可以描述每个人到‘西方’的距离,那么他的权力将与他所处的这一距离成正比。但是当社会决心排斥西方世界的时候(即上述的命运(b)),我们会感受到另外一种权力格局---如果存在一种社会心理度量可以描述每个人到‘传统’的距离,那么他的权力将与他所处的这一距离成正比。最后,更加复杂的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视角拉得很近(例如以十年为单位),那么很可能上述三种‘命运’同时展开它们自己的力量,于是我们会处身于不同命运的交错较量的旋涡之中。这当然也说明了一个基本的史学原理---‘历史’只在长期视角下才变得清晰起来(即变得‘可以理解’),与此相反,‘历史’只在短期视角下才变得可以解释(即无数细节问题得以澄清)。 关于人类发展的长期的知识结构演变和近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我就只能谈这么多。现在让我再回到人类长期发展的精神方面。如我所概括:给定总的能量投入及其增长速率,所谓‘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在特定的精神取向下实现的,由技术及其进步速率所转换出来的效用及其增长。所以,经济发展的尺度必定是精神的,而不能是任何外在于人的客观评价。 容格这样描述东方人的心灵:“这样一种内向的态度,总是要把目光从外部世界(已知或意识的世界)收回来集注于主观因素(即意识的背景)上,这就必然会唤醒自我的潜意识,即隐藏在对祖先和历史的特殊情感下面的‘考古类型’,以及这情感的升华---一种‘无限意识’,‘取消时间’,‘万物归一’的感觉。...这种与天道相通的感觉随着意识对外物的辨识越来越模糊而日益增强。”在容格的理解中,西方人的心灵与此完全相反:“...我们西方人的这种‘彻底的客观性’,如机器般地追求一个目标,一条理念,或一类原因,然后在生命完结的时候意识到为此而放弃的人生其它方面的幸福。在东方人看来,我们这种追求彻底客观性的人生显得如此苍白,...”(页499-502, Carl Jung,“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thinking”, in Joseph Campbell, ed., 斯坦福大学老经济学家西多夫斯基在近著<没有欢乐的经济>中指出:旧金山湾区各大学参加业余交响乐队的人数在20年时间里增加了五倍,大大超过了这一地区经济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物质生活只是人类发展的可以度量的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精神生活的需求与发展的速度几乎总是要大大超过人类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发展速度。 一方面是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迅速耗尽从外部强加给人类物质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效用函数的权重逐渐向精神生活倾斜从而在内部限制了人的物质欲望。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百年内,效用的主要部分将从物质消费的方面转向精神生活的方面,从而相同的资源(和不同的配置)将导致极为不同的效用增长。那时,西方人才真正有资格回答德克海姆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疑问:“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真的增加了我们幸福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人坚持以精神力量改造西方秩序以求获得人类合作的普遍的扩展秩序,才有了一线成功的希望。白色,这是古埃及壁画中死者在灵魂转世之前的颜色;黑色,这是古代东方大地之母的颜色。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流放以后,白色的西方将回归黑色的东方,获得新的颜色--- 介于黑白之间的颜色。这是西方的命运,更是世界的命运。在1999年完结的时刻,我为这一命运的降临祈祷。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观点分析 > 汪丁丁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