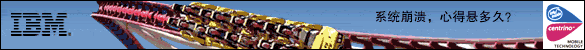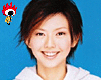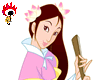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汪丁丁
一回到北京,各种“会面(meeting)”扑面而来,说是“会面”,也不确切,大多都是“会议”,所以附加了英文在“会面”后面,表 示两个意思都有。会面时,听了许多“故事”。例如关于“南街村”,关于“美国公司法”,关于某地的宗族,某人的姐姐,某某的信仰 ……尤其当与会各方发生意见争执时,讲“故事”就成了天然的支持 己见的论证方
式。但是问题马上就发生了,因为争论的双方都讲自己的“故事”,你说你见到过没有脚的麻雀,我说我见到过长了角的猪。碰到这种场面,许多人就开始出去抽烟或者上厕所。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能够交流?因为有“逻辑”这件事。当我说“ 正在下雨”时,通常人们不会认为我说的是“现在不下雨”。由简入繁,复杂的叙述要想让别人理解也必须符合逻辑。能够让人理解的复杂叙述,其逻辑链条连接着最简单的,诸如“A=A”这样的逻辑和所叙述的结论,这个逻辑链条被称为“理论”。
不幸的是,从最简单的逻辑,可以找到几乎无限多的逻辑链条连接到复杂叙述的同一个结论。“日心说”和“地心说”都可以解释行星轨道,欧几里德几何和黎曼几何都可以解释局部空间特性,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统一场论)并行发展,……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解释就更加如此,在每一个领域内都充满了互相竞争的理论。
当各种理论争持不下时,必须求助于经验检验。可惜,每个人在有限生命中能够经验到的事情实在是很有限。于是对各种理论的检验必须从一代人接续到下一代人,在积累着的经验中判断理论孰优孰劣。这就是“传统”。当我讲一个“故事”时,我的“故事”的意义在于它将新的经验加入了某个知识传统,它会合了传统里其他人的“故事”,要么支持某个理论,要么反对某个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故事”可以改变某一理论在传统中的“可信度”也就是被认为正确的“概率”。例如,我的故事在某个传统中已经是第一千零一次支持“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个人经验,而在这个传统里,已经出现过一百次不符合这条规律的经验,于是在这个特定传统中,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律”的正确性,在我之前应当是概率意义上的0.909,而在我的故事之后就变成了概率0.91,稍许加大了它的可信度。任何统计数据的意义都仅仅在于此。这是从休谟到波普的经验主义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作出的贡献。
离开了传统,我的任何“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就像“星球大战”里讲过的一个故事,皮卡德船长死活搞不清楚与他在蛮荒之地并肩战斗的外星人船长反复讲述着的“故事”。一直到那个船长在战斗中负伤死去,故事的语言和道德意义才被昭示给皮卡德。我在北京听到的那些“故事”,由于没有学术传统的重建和延续,显得缺乏理论意义,显得没有逻辑。我在一篇讲道理的文章里论述过海德格尔论述过的巴门尼德的“说”和“思”的关系,我的新意也许只是强调:“说”必须在一个“说”的传统中才有意义。同样,“思”也必须在传统里才称得上是“此在”的思。
强调学术传统的重建或延续,从西方学术传统中出来的中国人马上面临着阐释学悖论:语言是西方传统的,“故事”是中国本土的,怎么把中国的故事融入西学传统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我的看法。大致上说,我觉得取决于你所在的西学传统是什么传统,如果是纯粹的统计学传统,本来已经抹杀了样本与样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当然也就不会发生“本土化”的问题。西学中那些偏于人文方面的传统,问题就严重了。经济学似乎居间,“天命之谓性”,食色之性中外相通,那些主要依靠数据“说”的经济学家于是没有感到什么阐释学悖论。但是那些主要不能靠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例如研究经济制度的学家们,常常要讲一些“牛吃草”之类的故事,必须考虑西学传统与中国本土的故事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当文化差异可以决定人的行为差异时,在西学传统里讲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往往比讲一个精心化约了的简单故事更缺少意义。韦伯曾经感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一个细节深究下去,研究者都会遇到无穷无尽的因果链条,以致不可能满意地解释现象本身。正因此,研究者必须以无穷因果链条的某个适当的环节做为“有意义”的起点开始他的研究。所谓“数据(data)”其实不可能是彻底客观的,它只不过是韦伯所说的这么一种对研究者本人有意义的“起点”。仍然举经济学例子,首先对消费品做比较粗糙的分类,其中一类是书报杂志。如果研究者只关心收入水平与期刊销售的关系,那么使用统计方法可以得到结论说:收入上升到某个水平时,对期刊的需求量会加速上升。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消费品分类里,“期刊”这个概念对研究者的意义决定了关于期刊的“数据”的意义。如果研究者关心的是特定期刊的销售与收入水平的关系,那么首先必须加细“期刊”的概念,直到对所研究的题目成为“有意义”的(例如区分文学类期刊,体育类期刊和生活保健期刊)。不仅如此,通常还要求把“收入水平”概念进一步加(例如区分同一收入组内家庭的平均年龄或者性别比例)。在这个更深入的环节上,研究者很可能发现与上述统计关系不符甚至相反的统计关系,从而原来有意义的统计数据现在成为没有意义的。
最近听到不少批评西方人的故事,不过由于故事太接近观察者眼中的现实,包含了太多的没有解释清楚的因素,于是总是引起我对故事的理论意义的怀疑。最“简单”的故事莫过于“某西方人欺负了某东方人”,所以推论说“西方人不公正”。可是这里有太多的细节没有解释:姑且不说推论,只说作为“数据”的事实。为什么他欺负他(假定一个解释A)?为什么他为了A要欺负他(假定一个解释B)?为什么B会发生?为什么使B发生的原因会发生?……所以每一个复杂的故事都需要许多复杂的理论来解释,所以为了有意义,必须讲述简单的故事,必须在传统中讲述这个简单的故事,而且必须明确,“故事”的唯一意义在于对明确叙述了的某一理论的检验。这么一问之下,“谁欺负了谁”这样的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提倡讲故事要有逻辑,并不是否定故事的其他意义。其实只要听故事的人有感觉,不论是觉得新鲜,过瘾,甜蜜,还是觉得恶心,讨厌,没劲,这感觉本身就有某种意义。对于讲故事的人就更简单了,只要你讲了什么,你就发泄了什么,你就感觉到了什么,所以总是对你有什么“意义”的。
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条例研究就是讲故事。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必定是在学术传统内部针对某一理论的检验,或者针对某一没有得到解释的问题的说明。注意,“问题”与理论一样,都应当是传统的,其意义必须在传统中才能得到说明。因为所谓“解释”,就是在传统理论的假设和实验条件下,现象A如果发生,则现象B也会发生。所谓“没有得到解释”,就是在同样的理论假设和同样的实验条件下,现象A虽然发生,却没有观察到现象B的发生。离开了学术传统所定义的“正常关系”,现象A与B之间的“反常关系”就没有意义。
上述对案例研究的要求,不仅是对精确科学的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的要求。否则社会科学就不必带着“科学”二字,只须叫做“人文学科”罢了。不过,在具体社会里,时间是“历史时间”,理论的检验条件不可重复,所以检验的结果是支持还是反对预设的理论,常常要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我在《二十一世纪》里曾经读到过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大家早年经历的所谓“独母抚孤”现象的案例研究,印象很深。出身不同家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个人经历的文学家们的文学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年失怙”?这个案例研究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读者的主观判断,于是必须依赖于读者和研究者所在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个案例研究,我是倾向于赞同的,不过我赞同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体验。换句话说,在作为读者的我和那个案例研究的作者之间,研究结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其实建立在我们多少相同的生活体验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文学创作的某个“发生心理学”定理或者弗洛依德的“压抑宣泄”理论的承认和检验上。
所以,社会科学家研究本土问题,当他的西学传统与本土问题之间发生了前述的“阐释学悖论”时,社会科学的“人文”特点就凸显出来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定见。只知道必须在具体存在的传统中去“思”和“说”,只知道如果有人能够同时成为西学和中学两个传统中的人,他一定会有“大师级”的成就。知易行难,再说下去怕要被人认为忽视了“沉默的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