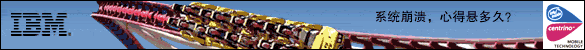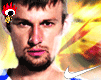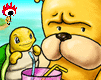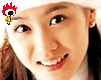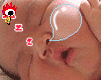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1日 14:10 中评网 | |||||||||
|
汪丁丁 经济学,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当它的“纯粹”形态的普遍原理被应用於具体社会的时候,总会引出“实践”形态的问题。现象学对纯粹科学的实证主义态度的批判,对中国经济学的意义在於:它一方面揭示出哈贝马斯( J ürgen Habermas )曾经强调的认知与兴趣之间的知识社会学联系,从而为经济学的话语权力划出合理界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实践理
九十年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含义 90 年代初由邓小平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广的“南中国模式”在整个 90 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论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与传统国营企业的激励机制相比,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对“分立的财产权利”( severance of property )的保护。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晚年曾对这一产权形态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数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产权形态以及围绕它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支撑体系,不应当误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被命名为“私有制”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制度”,而应当被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整个 90 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现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实质上就是这一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由於合作范围在人竤中的扩展,分工与专业化便得以深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为了在一个统一框架内理解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和纯粹私人企业的制度安排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率,根据西多夫斯基原理,我在附图( Scitovski diagram )中给出了三组曲线来说明这三种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如何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效率的。 假定一切生产行为都可以描述为生产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规范下的行为,假定附图的纵轴方向指示了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横轴指示了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那么在代理人可以选择的各种行动方案中,有三类是与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 1 )那些同时增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2 )那些仅仅增进委托人福利的方案;( 3 )那些仅仅增进代理人福利的方案。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类合作”的秩序可以得到扩展,当且仅当存在著第( 1 )类方案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第( 2 )和第( 3 )类方案的实现,那些旨在实现第( 2 )类方案的制度不妨叫做“奴隶制度”,而那些事实上极大地鼓励了第( 3 )类方案实现的制度不妨叫做“巧取豪夺制度”。出於明显的理由,这两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大范围的扩展;凡是违背个体自愿原则的制度,由於丧失了“合法性”,都是难以为继的制度。由於上述三类行动方案都是代理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实际上假设了代理人是“有合作意愿的”。 如我在附图中作的解释,代理人的均衡行为模式在这里主要取决於两个因素:( 1 )委托人福利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代理人的努力;( 2 )代理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这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已经包括了生产的技术结构(例如大规模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第二个条件则主要反映了生产的制度结构(例如团队内部互相监督的成本,外部人监督的诸方式)。代理人无差异曲线与行为约束的切点给出不同契约下的均衡——作为模式的典型行为,或者代理人的“行为模式”。在附图所示的三个切点处,代理人的不同行为模式为他自己和为委托人生产了不同水平的福利。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为约束的最高点代表了最大福利。可是由於存在著“代理人成本”,代理人的均衡行为通常不发生在最高点处,均衡点与最大福利点之间的差距就是代理人成本。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特征性的差异就在於它们表现出不同的代理人成本。 在“委托—代理”的各种可能形态中,“家庭”可以被视为是与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关系最接近的形态。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由於具有较小的契约监督成本(给定生产的技术条件),在附图所示的“委托—代理”诸关系中可以由最左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大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50 年代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拥有两万户农民,其监督成本极高,并且代理人的个体努力对“集体委托人”福利的边际贡献微乎其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由附图最右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小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而所谓“南中国模式”,或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可以由中间的那组曲线描述。 如果生产的技术条件一样,那么家庭或由最左边的曲线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但是家庭经济能够容纳的生产的技术条件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是诱致“人类合作”的秩序从家庭向外扩展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固然使用了大规模经营的技术条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监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销了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显出了为甚么乡镇企业或“南中国模式”可以成为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有效的驱动机制。 乡镇企业(比家庭具有大得多的技术规模)之所以具有较低的监督费用,除了因为依靠本地联系和血缘联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外,还由於它主要地实行了保护企业主管人员的“利润权利”的制度。乡镇企业有比较明确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的目标,所以由乡镇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代理人利润权利的保护导致了企业(计入“代理人成本”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国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如何发展和取代国有企业具有的那种大规模经济的技术条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投资机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润权利”呢?为著经济效率而定义的“利润”,也就是熊比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说的创新的利润或“价值剩余”。在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比特)和芝加哥学派的奈特( Frank Knight )看来,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所以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款来实行。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创新者的利润权利於是成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所谓“保护匿名的少数”原理)。 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对“剥夺者”的剥夺已经摧毁了这一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 1 )“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 2 )“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 90 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这在“南中国模式”中也表现得清清楚楚。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或“官商合理”论,或“南韩模式”)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辩护。 效率原则在“南中国模式”里,并且几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 9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则”发生著冲突。这种基於“经济增长是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好药方”的理念,即“南韩的增长方式”,是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无视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公平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发展总比停滞好些,并且“发展”始终是逼迫到中国人头上来的(“西力东渐”以及人口生育率转移产生的人均资源恶化);因此,我们必须为创新者找到“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由於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识份子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由於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我在下一节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以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中国自由主义”的出路 感谢 90 年代后期国内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与“新左翼”知识份子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处於双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著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宪法精神”里面,还缺乏对利润权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润权利的不受保护,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受到摧残,这也就相应地鼓励了权力寻租的能力和腐败行为。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提倡和坚持了苏格兰启蒙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立场视“产权”——由洛克( John Locke )定义的广义产权,即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视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视自由市场为文明演进的最可宝贵的制度遗产。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社会”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场社会,这里极容易发生资本与权势的勾结,从而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合法性基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的疏离和批判的态度,坚持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阐释的“启蒙”——对权力的(包括作为权力的“传统”本身)永恒的批判态度。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就一方面要对旧体制对人的奴役进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对新体制对劳动的异化加以批判。由於这一双重的任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在“中国自由主义”这里变得格外复杂,而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加以分类便显得没有意义。也由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双重的冲突与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国自由主义”。 我在另外几篇文章里已经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这里简要总结和发挥一下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提倡下列三件事情:( 1 )演进的普遍主义( 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 2 )作为对话的逻各斯( dialogue as shared logos );( 3 )交往的个人主义( 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sm )。 这三件事情当中,第一件关涉到苏格兰自由主义及“哈耶克—波普”传统的演进理性与康德普遍主义理性之间的某种打通或者某种中国式的折衷,以便在中国语境里讨论诸如“正义”和“自由”这类基础问题;第二件事情关涉到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要求培育“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希腊科学传统的中国科学很容易蜕变为“科学主义”从而破坏了科学精神本身。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尤其是赫拉克立特阐释过的大众“分享著”的和通过对话揭示自身的逻各斯,这在我看来是一条适合中国科学精神培育的思路;第三件事情关涉“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交往的个人主义不再是孤立的西方古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话展开了对话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一主体间关系(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为人格形成基础的个人主义。在我看来,这三件事情都与中国人的本性有某种亲密联系,因此不难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话语传统。 至於加上了这三件事情之后的自由主义是否还算是“自由主义”,我不能回答,不妨就叫做“中国自由主义”吧。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观点分析 > 汪丁丁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