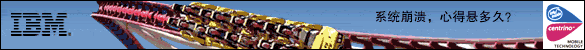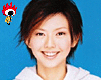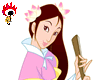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汪丁丁
记得我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常听到张五常教授雄心勃勃地谈论要 把港大经济系办成类似芝加哥大学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研究中心。听得 久了,不得不思考他这个雄心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思考必定引导着 观察,这篇随笔把我的观察和思考写出来,就教于读者。 “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或者广而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我认为,首先它必须是研究社
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学术机构,其次它 必须是在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学术机构。我试着提出这 两个条件所要求的一组“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的意义在于,我 们可以依了它们去世界上寻找那些真正可能成为学术中心的地方。 什么是“基本问题”?去掉冗长的文献索引,我可以“随笔”式 地说: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一个学科的全部历史并且推动着学科发展 的那些问题。例如在经济学中,“资本”问题始终推动着经济学发展 并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是贯穿于经济学全部历史的问题)。这个问 题的各种表现形式(表现为同样基本的问题)包括:利润问题或“租”的问题,劳动以及劳动的度量问题,生产过程以及生产的组织问题,人 力资本和知识问题,…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最终遍布经济学全部 领域(也正因此而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本就 是不可能解决的,研究者只是不断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 这些问题,从而不断地深化他们对整个理论的领悟。这是学术进步的 辩证法。
当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并且正由于其永远成为问题而推动着学术发展时,学术就形成了传统。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而形成的学术传统,必须通过学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如果这些学者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那么可以认为学术传统也就随之转移了(例如科学的中心从法西斯德国转移到美国)。为什么传统不能通过书本知识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引用博兰霓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家的观察。传统是关于基本问题的传统。那么是否一个人单独书就可以理解这些基本问题呢?当然可以,但是常常非常困难,尤其是当学术传统已经积累了几代人的时候。对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必须靠老师对学生的心智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必须使学生处于一种时刻包围着他的,渗透着对基本问题的关心的学术气氛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可能培养出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意识”。那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与基本问题相关的一切问题和一切事物的敏感性。没有具备这些敏感性的人,固然也可能在偶然情况下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深化对基本问题的理解,但是机会要比具备了这种敏感性的人小得多。这和不具备某种企业家才能的人与具备了那种企业家才能的人相比在特定方向上的创新机会微不足道是同一个道理。
怎样可以让学生们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呢?同发掘一个人身上的企业家才能一样,你必须让学生们对基本问题感到兴趣。这就涉及到所谓学术中心的“必要条件”了。一个人对基本问题有兴趣,也许并不很困难。人类共同的好奇心也许足够让任何人对任何基本问题感到一些兴趣。真正困难的,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在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安身立命”。这里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学可以讨论的,那就是所谓“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另一个超出了经济学范围,不妨名之为“终极关怀”问题。
学生是否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关于基本问题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去,在经济学的框架里,这取决于激励机制所产生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例如香港的大学生们,身边充斥着挣钱机会,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课余兼职,每月收入从几千到几万,看干的是什么工作了。除了考试期间,学生们大多不会安排课余时间阅读功课和研究习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大学学生是在“混文凭”,但求以最小成本得到一个关于“能力”的发信号权(signaling right)。香港是个商业化的都市,这里中高收入的工作大多是商业性质的。对研究基本问题的属于“软”专业人才的需求,虽然有一些,但需求量很小,报酬也较低。所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很少会有学生选择纯粹学术和研究基本问题。以港大经济系的课程为例,注册金融和货币银行课程的学生每年都在几百人以上。注册学习中国经济课程的也在三百人左右。但是选修博奕论或者比较经济体制课程的就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到了选修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时,注册学生就常常只有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了。
从经济学出发,我得到一个机构能够成为学术研究中心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它能够找到足够大的对基本问题研究的“市场需求”。这个条件,虽然俗气了点儿,但相当重要。它决定捐款的数量,学生的数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学生的质量。市场需求决定着一个学术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藏书和足够经常地与世界其它地方进行学术交流,以及是否能够把第一流人才从其它机构吸引过来。上述条件,适用于亚洲其它地方(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等)。这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对基本问题的关心和研究,是否可以靠了经济激励来推动?”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它的研究人员的构成是怎样的?”第三个问题是:“那些没有成为学术中心的地方,那里的学术研究是否可以有自己的传统?”为了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从最后的问题顺序向前回答。在没有成为学术中心的那些地方,学术研究的传统,至少这个传统的主流,只能而且必须依附于某个学术中心的传统,作为后者的“殖民地”而存在和发展(留学生,交换学者,访问教授,所有这些都只是“殖民方式”,我完全没有贬义地使用“殖民”这个词)。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便是纯粹应用的研究,也涉及方法论和假设体系的基础问题,也就是说,从应用工具的方法和假设一层一层地推上去,总会碰到基本问题。你如果不去研究这个基本的问题,你的方法和假设就是依赖于其他传统的。当其他传统中发生了基本问题和研究范式的变革时,你的应用研究的有效性也会随之发生危机。更进一步说,如果你完全不研究基本问题,你的学术传统是靠了什么问题推动其发展的呢?学术传统不是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一大堆具体问题的集合。学术传统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为它所在的特定社会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而为了能够提供这些手段,传统必须理解这个特定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海德格尔的所谓“being-in-the-world”),只有如此,学术才可能变成具体社会中存在的人的“上手的工具”。所以我可以声称:只要在一个地方存在着学术传统,它就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基本问题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研究基本问题。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被纳入一个整体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传统中的人对基本问题的理解。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员,他们的实践更主要地是社会现实的,正是通过他们在现实世界的经验,基本问题与特定社会发展的关系得以逐渐澄清。专门从事基本问题研究的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澄清不同的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把一个特殊的学术传统与其它特殊的学术传统沟通起来,从而能够提出普适性的原则。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从事基本问题研究,而在于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是否围绕着基本问题展开。在这个问题意识所营造的对话环境中,研究人员(应用的和理论的)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地方是否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
现在可以讨论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了。“问题意识”,这是一种对所要寻求的解答的意向上的引导,是一种对潜在的可能提供解答的研究方向的直觉。在那些学术研究中心,问题意识总是指向传统的基本问题,总是有一些具体存在于传统中的人,他们主要的关心是指向基本问题的,他们为基本问题而感到焦虑和冲动。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人,我可以借用哈耶克的术语称他们为“匿名的少数”,这些人往往不处在传统的主流中,他们往往是传统的“边缘人物”或者处在主流的敌对方面。一个比较自由的学术传统,有可能把这些匿名的少数人引入到主流学术机构中来,发动他们的学术创新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传统往往具有压制创新的倾向,边缘人物往往难以被主流人物接受。这样我得到学术研究中心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一个机构能够成为学术中心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容纳不同思想的充分竞争。
围绕着基本问题的“问题意识”的养成,还取决于学术机构所在的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黑格尔称之为“ethos”的东西。这里确实包含了终极关怀,但是也可以比较庸俗地用经济学术语说成是“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偏好和口味的培养”。康德在写作“三大批判”之前的很多年里,除了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授内容极其广泛的人文和科学课程外,每天下午的时间都消磨在当地上流社会的各种清谈沙龙里。德国能够成为当时欧洲的学术中心,就像雅典能够成为希腊的学术中心一样,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气质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例如读康德的著作,没有人能够无视其中浸淫着的强烈基督教气质。而我读到柯尔凯廓尔的《哲学断想》时,觉得那是一种被宗教情感压抑到几乎腐烂之后再发泄出来的人性。
我的讨论把我带到第三个必要条件:一个机构能够成为学术中心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它始终浸淫在导致了对基本问题的关怀的那种精神气质中。这已经不是经济激励可以提供的条件了。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南派和北派的学术风格,也反映出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南方的学术风气注重考据,分析,音韵。北方的学术则喜好义理,辞章,体系。所谓“燕赵悲歌”,“齐鲁鸿儒”,不如此不能相映出“楚风靡靡”。于是这些地方的学术在当地精神气质的熏染下各自形成了传统(及各自关心的基本问题)。
我在香港大学五年,我个人的感觉,学术中心的这三个必要条件在香港似乎都没有具备,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具备。首先,香港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商业导向的,不是人文发展导向的。用珀特尔的话说,香港还处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能否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如日本和德国)和最终进入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如西欧各国),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香港缺乏对基本问题研究的市场需求。其次,香港沿袭英国制度,学术研究制度比较僵化,“名牌”导向,所以在学术界不能充分发挥出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精神。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香港的社会文化传统中缺少那种可以使人对基本问题产生关怀的精神气质。
那么北京呢?似乎在第三个必要条件上比香港好得多。学术思想的自由竞争则依学术领域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至于对基本问题研究的市场需求,我不知道是足够还是远远不够。上海或其他城市,我了解的就更少了。对现实虽然不够了解,信心还是很足的,相信中国本土的“泱泱大风”能养育出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当然,关键还在于努力去创造学术中心的前两个必要条件。否则的话,任你怎样反对“后殖民”,你也难免“后殖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