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的探索 在天则所成立十周年之际的反思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1日 13:30 中评网 | |||||||||
|
樊纲 天则创始人之一 天则所理事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天则十年了。我们这些与天则有关的人,都会有诸多的感慨,也都在反思这十年的历程。 一.一批研究制度的人探索着在自己的身上应用制度
天则所把一批研究各有侧重的人联络起来的那个“点”,是制度,是因为这些人对制度、对制度研究的关怀。也正是因为这一个结合点,天则的特点不仅在于对制度的研究,而且可以说是对制度问题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各学科的人,只要对制度问题相关,都可以参与天则的项目,都可以到天则的讲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天则研究所本身就是一个制度。这些年天则的发展过程,也是天则这个研究所制度完善的探索过程,是我们自己在天则这个制度内看到制度的作用从而更加相信制度作用的过程。 我最初五位发起人之一,也就是最初结构中的“股东”之一。但是我后来辞掉了股东身份,原因是我成为了一个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个研究基金会是可能对天则所的研究项目进行资金资助的,这就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由我任秘书长的基金会给我是股东之一的研究所(公司)进行资金资助,会导致潜在的腐败的可能。于是我提出的辞呈,理事会和股东会作了研究,大家都同意,尽管在法律上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的条款,尽管大家可以信任我这个人的道德情操,但在一切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上,应该也必须依靠制度的约束,对我有好处,对天则的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对我们推进制度建设的进程有好处。于是提议获得通过,我不再是股东,只留任理事。天则的理事本身是一个公益的工作,没有任何的金钱往来。 我本来就没有为天则的建设付出很大精力,不当股东后就更是没有再作什么工作。应该说,天则这十年,主要就是在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三位的全身心的投入下走向成功的。象我这样的理事会成员,基本上没有作什么工作,只是在分享由他们三人所创造的荣誉。但天则所一直坚持了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的制度,并且确实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制度。1997年的一天半夜,张曙光突然来电话,说常务理事们在是否接受南德公司赞助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第二天又必须作出决定,因此决定按照制度规定提交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于是,第二天一早7点,我们全体理事从四面八方赶来,最终通过投票表决做出了不接受赞助的决定。这个决议本身是否正确,另当别论,这个事情所体现出来的是制度的作用和我们依靠制度的必要性――在利益一致、观点一致的时候,制度的作用是隐形的,可能都会被人认为可有可无,认为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制度只有在利益冲突、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才发挥着明显的作用。其实这正是制度的本意――制度就是为了调解和调节利益冲突而在事先明文定下来的行为规则。 这些经历也是一种知识,一种关于制度的鲜活的知识。天则所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取于它是否能将自己的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 二.知识不一定能为自己挣钱 在天则十年之际,盛洪感慨道:天则的奇迹,就在于它存活了下来。这是肺腑之言。但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自己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这一认识与我们当年发起天则时踌躇满志,坚信“有了知识一定能挣到钱”(从而能用这个钱来养研究),有了一个极大的反差。而且在事实上,这十年,也是天则从一开始的搞商业咨询与搞学术研究并举,转了一圈回到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定位上来的过程。为什么会是这样?其中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仔细分析一下天则的这几位骨干份子,应该说都是一些典型的书生,是一些一天到晚想的是作学问的人,关心着一批非常抽象、非常学术的问题;对实际问题的关心,也都主要限于那些公共政策,在于那些与制度而且主要是公共制度有关的问题。这是这批人的人力资本的特质。 学术研究属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范畴,公共政策研究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而所谓学术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它们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这种物品的特点就在于,它为社会提供的收益可能是很大的,但这种收益是由社会全体、众多的人群和利益集团所分享、所共享的,而每个人的收益大小是很难界定、很难分别计算的,因此要为这个物品定价,要让人们来为其付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商业咨询所提供的是私人物品,为一个私人或一个公司所独享,收益也就容易定义,人们从中“挣钱”,当然要为此而付费,相对较为容易(不容易的是你是否能使对方真的感受到他从中可以受益,而且承认这种收益)。 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人力资源的特质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你的那个知识的确是可以“挣钱”的――使整个社会更好地挣钱,挣大钱――但是却不一定能为你自己挣钱的,除非有一种机制能够将社会收益的一部分有效而合理地从众多受益人那里转移过来。 这自然让我们想到了政府与税收机制。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将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政府研究,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过去我们的体制的主要部分。 但是天则的这批人看到了传统公共研究机构的弊病和只有公共研究机构的不足,立志于探索一条新的“用咨询养研究”的道路,也就是由提供私人物品挣到的钱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 这是否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呢?应该说是的,是可行的道路之一。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确有一些私人机构在从事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学术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为社会服务。 但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基本的一条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知识结构要比较全面,要是“全材”,既能作咨询,又能做研究。这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如此,它可以是一群人中不同的知识资源互补,有人作这个有人作那个,在一个体制内相得益彰。 由此来对照,天则这十年来探索“用咨询养研究”道路之所以在经济上较为困难,是因为这批人的知识过于“同构”,这种同构的特质又在于太为书生――骨干们都没商业的知识和经历,学术情结又极为强烈。总之,他们的知识,或许是能使别人挣钱的知识(通过增进大家的科学知识,通过推进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而不一定是能使自己挣钱的知识。 因此,天则后来的定位调整,是对的,是大家最终承认,这批人可能不适合走“用咨询养研究”的道路。 三.专业分工的新机制:如何让资源通过非政府的渠道流向学术研究? 那么,是否应该使天则的这批人通过学习商业咨询来改善知识结构,来走好“以咨询养研究”的道路呢?我想不必。第一,这对于这批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第二,我们应该相信任何特质的资源都会有其特殊的功用,没有必要都是全才,“全才”由于缺乏专业化的优势,可能反倒是庸才。甚至,第三,天则也没有必要非要通过引进其他人材形成资源优势互补。那些能作商业咨询的人愿不愿意到一个由学究们领导的机构中来为学术研究挣钱,且另当别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是否有别的道路更适合于这样一批人的特质。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以多样化的制度去有效利用多样化的资源,而不是让资源同构化去适应单一的制度。那是计划经济试图做的傻事。 除了政府资助研究,商业咨询养研究这两条已经讨论过的道路之外,另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被证明可行的道路就是专业化分工之路:能挣钱的人们专业化地挣钱,然后在一定的机制下将一部分利润捐给学术研究基金会,以资助学者们从事专业化的研究。不妨称为第三条道路,或“私人捐助养研究”的道路。 这条路应该说已经开始在中国形成了,但要有大的发展还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形成。它们是: 第一,经济有大的发展,私人财富有较大的积累。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在一二十年后的捐款,可能是这一领域的真正的“第一桶金”。 第二,形成有利于私人捐款的制度,比如说对公益事业捐款可以减免所得税、遗产税的制度。在这方面我们还差得很远。 第三,在社会上形成“把大的财富留给子女是害了子女”的观念。 等等。 天则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天则的探索,以及我们其他一些非政府研究机构在研究体制方面的探索,都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我们正处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体制正在各个领域里不断形成。这正是我们这些研究制度的人深感兴奋和激动的原因,也正是天则的生命力所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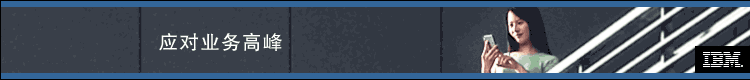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观点分析 > 樊纲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