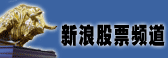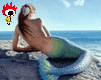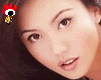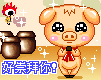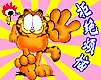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郎咸平不讳言有“成名”想法:我不想表现脱俗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30日 10:17 瞭望东方周刊 | |||||||||||||
|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范无盐/北京报道 3年前,香港学者郎咸平初入内地,便以“炮轰”德隆扬名股市。3年后,郎咸平又将枪口对准新目标: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同时,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复星以及南京斯威特悉数受其“关注”
“民企杀手”所过之处,老板心惊肉跳,股市因“郎旋风”再掀波澜 “郎咸平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8月上旬,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以诽谤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再次将郎咸平推向舆论中心。 “顾郎案”最新进展如何?郎咸平频频发难民企的背后有无利益牵扯?8月24日,郎咸平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及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做出回应。 郎咸平说,“从小到大,我都不是精英,我不过是个苦读的书生,这种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你是在“作秀”吗? 《瞭望东方周刊》:国内公众对于香港高等法院受理“顾雏军状告郎咸平诽谤罪”一案非常关注,不知此案最新进展如何?案情是否影响了你的正常工作? 郎咸平: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公众对我非常关心,也替我担忧,我内心觉得非常温暖。其实这个社会对我的关心也正是我奋斗的原动力。大家不用担心香港的诉讼,只要一切依法处理,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讲个笑话,我的律师很高兴接到这个著名大案,因为可以增加他们的知名度,他们还将律师费打了个大折扣。这件案子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我依然会按照我先前提出的理念对上市公司作出学术性的批判。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郎事件”之后,有的媒体称你为“郎监管”、“孤胆英雄”、“民企教父”、“流氓教授”和“三无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郎咸平:外界虽然给我戴了很多帽子,但是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做了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 现在的局势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我很担心媒体会把我推向一个神台,我并不是要拿着道德的利剑,来挥砍这些企业家,因为这根本不是我的专业。坦白讲,我的贡献就是用数据说话,仅此而已。 有些媒体质问我为何不对这些批评我的经济学家作出回应呢?难道我也“失声”了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有些只谈理念而不用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在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有些经济学家竟然可以天马行空,随便乱谈理念,我感到很震惊,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可是如果我也降低到如此水平和他们争辩,那不正是违反了我多年所推行的用数据说话而不妄谈理念的追求吗? 但不幸的是,这些不用数据说话只谈理念的经济学家竟然是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这种仅谈理念的治学态度和拍脑袋又有何本质上的不同呢?而这种拍脑袋所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让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依据,真正是个“清谈误国”。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媒体公布,有“作秀”、“炒作”之嫌,你如何应对这种质疑? 郎咸平:自从2001年底我决定来内地发展时就发现,这里的企业管治环境和美国大不一样。但问题是我的专业研究就是做公司治理,由海尔、TCL和格林柯尔的案例,读者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我坚持做我的专业研究,在中国目前不成形的企业管治环境下,就一定会发现上市公司侵害国家利益和中小股民权益的证据。 我事先也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因此,我似乎只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每天混混,放弃我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和企业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团和气,还可以有不错的回报;第二呢,就是继续坚持学术独立,认真做好研究,而且把结论负责任地告诉公众,仅此而已。我的研究虽然造成了轰动,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诉讼、挖墙脚和人身攻击等等,这也是我目前正在经历的。可是这就是我当初的选择,因此我不但不会怨天尤人,我还会坚持走下去。 另外,如果你有一项研究成果的话,你也会有两个选择:披露或者不披露。披露的话,有人就说是炒作,那么我怎么才能把它披露出来,又不炒作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有企业收买过你吗 《瞭望东方周刊》:有句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你做这种研究并公布出来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郎咸平:实际上,我没有选择,你做这个研究,就必须关注上市公司,发表了,就这结果。那你说,我是不是出于利益来做事情?我的回答很简单:就算我对哪家公司有好感,我也不能说这家公司好,除非我有数据支持;就算我讨厌哪家公司,我也不能说它坏,除非我有数据支持。由于我是靠数据说话,因此就基本上排除了利益和我研究挂钩的可能性。而且为了维持我的客观,我在2003年以后已经回绝了上百家企业独立董事和顾问的邀约,我未来也不会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与顾问之职。 但是,这种靠数据说话的研究依然可以有很大的市场。我的秘书张琳会和企业讲得非常清楚,我上课是要收钱的,演讲也是要收钱的,明码标价。而且我是根据数据说话,在场听众觉得尴尬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科学态度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我必须说,我的这种科学治学的态度,反而得到了相当多的企业家的尊敬,也创造出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也就是因为这种明码实价,非常坦率,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反而不会对我有什么负面的评价。大家都知道我对民营企业的批判是最严厉的,但是最喜欢听我课的人反而是民营企业家,这可能会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很多被我骂过的企业家反而非常诚恳地邀请我讲课,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研究结果对他们有益处,他们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改善公司运营。这就是我创造的一个独特的市场。而且大家已经知道我的原则,我在任何场合都是靠数据说话,不存在人身攻击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企业赞助你的研究? 郎咸平:从来没有。我的研究都是香港特区政府赞助的。我在长江商学院只是上课,也没有企业利益牵扯。但是我并不反对企业对学术研究的赞助,这在国外也相当正常。只是当你接受了某企业的赞助后,下次在公开场合不要针对该企业发言就是了,这也就是国外所推行“阳光法案”的基本精神,也就是避避嫌的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遇到被企业收买的情况? 郎咸平:从来没有企业收买过我,也从来没有企业找我帮他们做研究。他们通常都是抹黑我、丑化我、诬告我,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这也是我比较倒霉的地方。 因为教学需要,这些研究都是我自己指导学生做的,有些企业比较有名,大家又比较关注,我就指导我的学生做。我所有的案例都是自己花钱做的,从没有得到过别人的支持。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介意透露一下你目前的收入来源? 郎咸平:我出去讲课、演讲都是要收费的。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好透露,一透露,我就没有私房钱了,对不对?现在外界对长江商学院邀请我去企业讲课的出场费有很多传言,各种版本都有,说会达到六位数字啊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瞭望东方周刊》:这相当于“明星级别”了? 郎咸平:这个绝对不敢当,外边很多传言我的出场费是全国最高的,我都不置可否。但和张惠妹、谢霆锋相比还是差很多。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在长江商学院的年薪呢? 郎咸平:按照我们签订的合同,我是不能披露的。我只能说,比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收入要多一点吧。我们不要老是在钱上打转嘛,谈谈其他问题好不好?我赚的这点小钱哪能和我国民营企业家相比呢?说多了,他们要笑话我“赚这么少钱,还敢到处穷吆喝”。 你是想成名吗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之所以敢大胆直言,是因为你不像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一样受到利益因素的制约? 郎咸平:不是那么单纯的,不仅仅是敢说不敢说的问题。如果你有了一个研究成果的话,你会面临两种选择:说,或者不说。选择不说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成名,永远都不会对这个国家有任何帮助;而选择说的话,你只会得到一种结果,就是接受公众以及经济学界的质疑。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提到,如果选择“说”的话,可能是为了成名。那么,你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有没有成名的这个想法? 郎咸平:当然有啊。如果说不想,那不是太矫情了吗?“退而独善其身,进而治国平天下”,哪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想做这种事呢? 《瞭望东方周刊》:郎教授,你谈话很直率。 郎咸平:这个世界上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不想表现出做什么事情都很脱俗、很高超,做事情都是为了什么什么理想之类的。我是学商的,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也是个比较庸俗的专业。毕竟我也要有个人的理念需要完成嘛。 你要为民企指明什么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撰文对你研究问题的性质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郎教授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是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不知你如何回应这样的观点。 郎咸平:如果他能提出点数据来批评我的话,我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也愿意和他讨论。这么空洞的话怎么回答呢? 《瞭望东方周刊》:有经济学家指出,你对民企的反对态度源于你“不了解中国社会、没看清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你认为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郎咸平: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民营经济,只是说,民营经济必须在法制框架下得到约束,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民营经济具有掠夺性,它在不断扩大、不断掠夺的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 对于这种观点,我想反问一句,你认为美国的民营经济是对的吗?如果是,那好,菲律宾遗传了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民主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民营经济制度,但是你到头来会发现,因为法制缺位的问题,菲律宾国内出现了大范围的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把老百姓逼到必须到别的国家做佣人的地步。这是你想要的吗? 菲律宾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极端的坏例子。民营经济最好的例子是美国。 美国的民营企业与菲律宾不同,它在法制化的框架下运作,必须遵循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它能很好地运行。 我现在批评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核心在哪里呢?就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如果任由这样的民营企业走下去,我们只能走向菲律宾。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最有效率,它的效率体现在哪里?两方面:第一赚钱很有效率,第二剥削财富也同样很有效率!而这点正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看清楚的。因此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让民营企业走上菲律宾式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在对民营企业的效率保持警惕的同时,你似乎特别看好国有企业,那么,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来自哪里? 郎咸平:我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贯是一视同仁的。 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我做过研究。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一些国有企业,它的绩效不比民营企业差。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出,国企的总资产回报率是4.1%, 而香港民营企业是4.3%, 这个数字国企差一点。但是从单位资产创造的市场价值看,内地来的国企是1.13倍,香港的民企是0.97倍,这方面国企要好得多。 一个是总资产回报率,一个是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这两项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国企毫不逊色啊。我们不能拿5年前的国企效率来看今天的国企,现在有些上市的国企真是浴火凤凰,表现挺好的!我们一心一意地要走民营化的道路,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国企这几年也在学习,也在突飞猛进。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产业走向必定是以大型国企、中小型民企为主导。国企规模大有着历史的原因,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并作进一步的理解与研究,而不是打倒。我认为社会各界应该正视大型国企老总比民企老总更为用功学习的事实,至少这是我多年培训企业老总的心得。在香港,相当多的上市国企老总的学习精神是让人感动的。 我想反问读者一句话,你们认为由我们目前所熟悉的民营企业家去经营这些大型国企能做得好吗?这方面我很难相信民企神话。中国民营企业必须学会安身立命,不要想到在几年内做到世界500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500大的公司要经过几乎上百年的积累、学习与磨合才能做到如此之大。当然,很多对民企有信心的人又要跳出来跟我吵,但我只想回应一句:“光有信心是不行的。” 为什么别的经济学家发现不了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国内企业界出现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你可以发现,而别的经济学家就发现不了呢? 郎咸平:发现企业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那也是像经营企业一样需要多年的积累。真正的原因在于我掌握了三点“秘笈”。 第一,要找到切入点。在做学术研究时,由于世界上人才济济,你能想到的切入点,大概别人也都想到过了,因此,经济以及金融学领域的情况和物理化学领域截然不同,发表学术论文是非常艰难的。只要能发表3到4篇一流期刊论文,就能拿到名校的终身教授,可见发表论文的难度有多大。我之所以能跳出原先的框框找到新的切入点,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完全得力于我的学术积累,仅此而已。 第二,即便是找到了很好的“点”,也必须透过严谨的逻辑分析与推理,当然,这也不是我比较聪明,而是我在这方面也得力于沃顿商学院的折磨与训练。当然这种训练的完善也需要持续的积累。 第三,就是数据支持。我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是有数据支持的。 这三个加在一起,在国内看来是很新鲜,实际上国外学术界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他们看不出来企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 郎咸平:技术问题是一个难关,但经过学习与积累总是可以突破的。 《瞭望东方周刊》: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郎咸平:我当然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非技术上的原因。以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也是非常艰难的,绝对没有一点侥幸。其实我的命也是很苦的,目前表面的风光背后,却是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我从1986年拿到博士学位到现在,18年过去了,才分析到现在这个地步。而且在这18年里,我一直没有停止过,一直在不断地做研究。其实我的学生对我比较佩服的一点是,我周末一定在办公室做研究。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很苦的书生的日子,一点都不值得追忆。这也是我很少鼓励学生去念博士的主要原因。我目前已经没有选择,我希望往后更加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案例,以便于企业学习与改进。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也有很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他们也受到过国际上这种严谨的学术训练,难道他们就没有掌握这些学术方法吗? 郎咸平:的确有这样的学者。不过,他们可能会从各自的角度来谈企业出现的问题。他们是搞其他方面研究的,而我是学公司治理的。他们可能会看到企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做营销的,可能会谈营销。我是做治理、做战略的,我就谈我这方面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企业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领域不同的经济学家也是应该能看得出来的? 郎咸平:他们看得出看不出,是他们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谈我的专业,我主要看企业怎么剥削股民啊,怎么剥削国家财产啊这些问题,这些是我的研究专业。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事件发生后,国内经济学界好像没有什么反响,有的媒体认为这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郎咸平: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谈论太多,老实说,我也有点纳闷。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这个企业还没有做过深入调研,不知道该讲什么,这可能是主要原因吧。 坦白讲,现在在中国,做这些企业案例研究的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事实上,我做企业案例所运用的方法论是我自己创造的,用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开数据,经过我的模型,经过我的推理,来判断这个企业在干什么。所以这条路走起来也比较辛苦,因为没有前人的脉络可循。但是我对做这件事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尤其是能得到企业家以及社会大众的认同,这似乎比什么都重要。相对而言,国内经济学家是怎么看我,似乎就比较次要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是否曾经深入到企业内部,对企业进行过实地考察? 郎咸平:没有。我不是做行销的,不需要和他们谈。因为我需要的东西,像各类数据和模型什么的,都已经有了,只要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而且极准,我相信透过TCL、海尔以及格林柯尔等案例,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我的分析方法是有极强的应用性的。但是如果我对数据有疑问的话,我通常会和相关企业交换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公司提供的数据不真实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做判断? 郎咸平:对他们披露的数据我会认真审核的。比如说TCL这5年之内的报表,我会从各种不同角度来测量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的。这是个基本功。一般来说,对于企业的数据,你要想全部伪造是很难的,伪造一部分有可能,但这是可以查出来的。这些基本工作我都会做,什么时候我会跟企业谈呢?就是当我对这些数据没有把握的时候,比如前后数据对不上的时候,我会跟企业谈,当然不是很多,占三分之一吧。 相关报道: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财富人物 > 郎咸平质疑顾雏军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