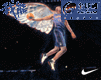| 董事长谢幕以后 失落焦虑还是退而不休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3日 09:54 中国企业家 | |||||||||
|
有的人在焦虑、失落中忙着找寄托,有的人在充实、激情中退而不休。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几乎一转眼,当年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们就老了。
今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纷纷退位,欧阳忠谋(普天集团)、王之(长城集团)、赵新先(三九集团)、倪润峰(长虹集团)、罗开富(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等等,公开的理由都是“年龄到了”。资料显示,超过60岁的大型国企领导人尚有20余位还在位。尽管有人认为根据年龄“一刀切”太过简单,但目前他们的命运不大可能改变。 舆论对他们的离去颇多留恋。这些董事长们为人瞩目,他们在自己的任期内通过资产重组、上市等手段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世界500强的梦想正在得以实现。然而正当他们大刀阔斧之际,不知老之将至,岁月无情,临谢幕之际,想必董事长们定会心情凝重,很多人甚至尝试通过MBO(管理层收购)来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把自己留在那个熟悉的舞台上,但到了不得不谢幕的时间了。董事长们情绪复杂,罗开富在即将接到免职令时表示愿意接受本刊采访,之后再无消息,大概是三思之后的结果吧。 民营企业家的“退位”与此不同:没有年龄限制,而且大多退而不休。“企业是自己的,无所谓退休不退休。”这是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态度。当记者与高层早已接班完毕的万向集团、格兰仕集团联系采访时,对方很惊讶:鲁总(鲁冠球)、梁总(梁庆德)没有退休呀,他们都还在一线工作。 华西村还需要吴仁宝吗? 76岁的吴仁宝说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半退”,他表示自己要干到80岁。“本来领导鼓励我说能干到100岁,群众的话就不太好说了,他们说我最好干到千岁。”吴仁宝说,比起当一把手的时候,担子看起来轻了—原来既要思考又要实施,现在更多时间在思考,而实际上,“我必须让华西村继续好下去,责任更加重大。”吴仁宝说自己跟有的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继任者做得比自己好会不高兴。华西村“好像一棵自己亲手种起来的树,怎么舍得砍掉呢” ? 半退下来以后,吴仁宝说自己做了几件好事,其中之一是解决了“五种户”的问题:个私户(只想自己,目无组织,不要领导)、贫困户、拆迁户、红旗户(小康人家)、不想户(混混)。吴仁宝的目标是让这些人都各得其所,跟华西村一起进步。其中教育“不想户”的方法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不好意思,纷纷要求就业。 每天,吴仁宝都要给来华西村参观的人们讲演。少则一场,多则三场。他尽可能地满足大家对他的“观赏”要求。 “我没有时间玩儿,每天忙得很。去国外考察也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年轻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尽量补回来。”灵山大佛离华西村很近,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去处,吴仁宝一次也没去过。“我不靠神。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修行。”半退之后,吴仁宝跟村民接触得更多,“听到的话也比以前多了。” 上了年纪,以前因为工作方法不当曾得罪过的人让他耿耿于怀。“要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多年以后,对方的谅解让他如释重负。“已经纠正了不少了,心情很舒畅。” 吴仁宝的生活“没有规律”。“有了规律,违反了就对身体不好;没有规律的人就不会受影响。”他每天早上3点甚至更早就起来,精力充沛,觉得自己好像又年轻了。“我给新领导班子提建议,采不采纳由他们定。” 吴仁宝住的还是老房子,分得的奖金一分不拿。“我的乐趣就是为人民服务。” 有了更年轻、更有文化的领导者,华西村真的还需要吴仁宝吗? 老人家想了想,说:“你去村里问100个人,至少有98个人会说我好。” 吴仁宝嗜烟,一天要两到三包。据说刚检查完身体,“一切正常”。 徐传化和他的传化艺术团 离华西村不算太远的杭州萧山瓜沥镇,晚九点。70岁的徐传化坐在“传化艺术团”的露天舞台上,双手交叉下垂,身边是发出强劲音响的硕大音箱。歌舞戏曲轮流上阵,灯光变幻多端,徐传化姿势不变,对耳边的巨响充耳不闻。“他在团里岁数最大,可是比我们都认真。”徐传化的侄子徐观泉(也是艺术团的演员)说,“比如我们在小品中要表现敲门,一般就是用嘴发出声音就好了。他觉得我们表演得草率,主张用鼓点。每次,他都紧盯着演员,手里拿着鼓槌随时准备配音。” 一个由徐传化琵琶伴奏的莲花落节目开始了。如果不细看,你根本发现不了老人是在用一根手指拨弦,其速之快,不让正规的五指轮动。“他60多岁开始学琵琶,手指已经没有那么灵活,学不了轮指了。”徐观泉说。徐传化不识谱,为了能用琵琶伴奏,他让人把谱子写下来,自己跟着录音机一点儿一点儿对,而且经常是半夜两三点就爬起来练。 徐传化能拉二胡,会吹唢呐。“传化艺术团”就是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发展起来,于2000年正式挂牌。邀请他们表演的单位很多,而且多数是非政府机构。邀请方要求的演出内容通常是宣传计划生育、交通安全、城乡一体化等。艺术团差不多每天都有演出,邀请方会出一些车马费,但总体上艺术团是亏本的(如果不算它的广告效果)。徐传化每天雷打不动,在舞台上的位置不变。艺术团的每一个节目都要经过徐传化的审查。 虽然看上去比吴仁宝轻松,徐传化也没有完全脱离传化集团的领导工作:“我每年都有5000万的销售任务。”他跑销售出身,传化集团产品最初的市场就是他打开的。 “我每天都见不着他。晚上12点多回来,早上6点多就走了,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徐传化的老伴说。像吴仁宝一样,他们住的还是建于20多年前的老房子,位于厂房的后部,楼门前晒着玉米棒子,院子里养着200多头猪和数量众多的鸡鸭—这些都是为传化集团的食堂饲养的。 徐传化的老伴对他说:“你别搞演出了。”徐传化说:“你别养猪了。”结果,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得其乐。 每天早上,徐观泉来接叔叔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一份印刷物的空白处“临帖”认字。“我从小苦出身,不识字。”徐传化说。就这么坚持下来,居然报纸也能大致读下来了。 瓜沥镇的这次演出很成功。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开着摩托前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音箱边上,徐传化对此无动于衷。包括他自己在内,有谁在意他是一个新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呢?他就像是一个零件,安静而有耐性地工作着。 每个董事长退休之后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生活,吴仁宝和徐传化只代表他们自己:朴实,甚至可能固执;没有退休的失落,没有暮年的死气沉沉,有时候天真烂漫;拥有大量财富,甘于普通人的生活。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但这一切,好像现在已与他们无关。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财富人物 > 《中国企业家》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