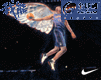| 我的父亲母亲:老上海钢铁大王的女儿讲豪门深宅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2日 08:04 外滩画报 | ||||||||||
|
外滩记者刘莉芳 吴春燕(实习)/报道 五原路,是市井的,也是优雅的。和朱文琪打的顺着五原路开,朱文琪是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朱恒清的二女儿,今年67岁。她在这生活了五十多年,熟悉窗外任何一个细节,甚至能精确地告诉司机,×××路口的绿灯一次能开过××辆车。
从五原路的西段开往东段,对于东段,朱文琪的微词是显见的,那是每个来自西段的人的同感。这条马路,以乌鲁木齐路为界,东段的气质是市井的,原先这里有一座颇有名气的菜场,在那里能买到不少其他菜市场买不到的高档吃食。现在菜场早已撤离,但菜场那种喧闹嘈杂的气氛还未完全褪去,马路两边的小店也带有菜场的余韵。西段则幽静许多,住宅以老公寓与花园洋房为主,许多精彩曲折的故事都深锁在一座座看起来无奇的房子背后。 朱文琪的家就在西段。去年圣诞节前,第一次采访她,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五原路最大的那扇铁门后面就是她家。亲眼见后,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不能迟到,因为她的住房离铁门有十米,如果没有约好,任我在外喊破喉咙里面也是听不见的。和朱文琪断断续续地保持了一年的联系,也断断续续地了解了她的故事、她的父亲、她的家族。 我的父亲 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朱恒清 那扇铁门背后,是一幢白色三层的楼房,墙面上清楚可见“文革”时期的大标语,楼前就是一座花园,旁边是个葡萄藤架,花园与墙外几幢八九十年代的建筑紧紧挨着。铁门里已没了往日顾盼流连的风致和雍容淡雅的仪态。朱文琪告诉我,原来的花园比现在大好几倍,大门是开在前面的复兴西路上的,花园里还有两个网球场。 朱家老楼原来是意大利的总会,当时只有一排一层的平房。抗战爆发后,意大利人撤出了上海,父亲朱恒清就买下了这块地皮。后来在半闭钢厂的那段困难时期,父亲干脆把它租了出去。请人重新设计翻造了这幢三层的别墅,一直到1948年才建成了现在的这所房子。1949年正月,母亲陆英娣选了黄道吉日,一家人搬进花园洋房。在这个花园光景最好的时候,它只是周末让一家人来度假用的。他们家一直住在北苏州路那个中式大院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搬了过来。 朱家祖辈是无锡的有钱人家,祖父朱士川是无锡荣巷镇朱祥巷人,到了太平天国时,一场大火烧了整个村子,朱家从此败落了。1902年,朱恒清生下来八天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他从小由二姑母带大。而祖父朱士川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无锡老家,到上海来谋生。 1920年,朱恒清也到了上海,在亲戚介绍的源椿号里当学徒。当时所谓铁号并不是打铁的铁匠铺,而类似于现在的大、小五金店。那时上海的很多铁号都是无锡人开的。朱恒清学徒期满后,留在店里又干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就出来单干了。1930年,朱恒清开了一家店——恒馀铁号,生意越做越大,店面由一间变成了两间,店址设在北苏州路608-610号,沿街面房做铺子,院子做货场,再往里一进院子是家人住的地方。老太爷朱士川就坐在店里帮忙看看店。他活了81岁,1959年才去世。 1940年,朱恒清感到单纯经营铁号总是要仰人鼻息,看外国人脸色吃饭。于是在他的发动下,联合了几十家大小铁号,成立了茂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厂于长寿路111号,设事务处于北苏州路670号。钢厂以轧铁、生产竹节钢为主,雇佣工人90余名,月生产量300余吨,主要客户为交通部属下津浦、京沪、浙赣等铁路局、江苏省工部局,还有一些大的建筑公司、纱厂和各个五金铁号。这样既解决了自己内部销售需要,不再依靠进口,而且反过来变成了供货者。茂兴发展得很快,不久二厂又投入了生产。 朱恒清虽然是钢铁厂的发起人,但觉得自己资历不够,所以请张鸿勋出资做大股东出任董事长,朱恒清任厂长。随着朱恒清地位的逐渐稳固,他开始从各个小股东手里买下他们的股份。就这样最后,他手中的股份达到了近90%。他终于成为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了。 从一个小小的铁号老板,到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朱恒清大字不识,朱文琪至今仍难以想象父亲是如何做生意的。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哥哥开车去相亲,她哭着闹着也要跟去。爸爸哄她就带她一起去谈生意。“我只记得老长老长的一张餐桌,英国人和爸爸坐这头,我坐在那头。她吃着西式菜点,他们谈生意,父亲在做学徒时就自学了英语。后来才知道,在这个餐桌上,爸爸从外国人手里买下了三条旧洋轮,来拆取上面的钢板。”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吞并朱恒清的茂兴钢铁厂,朱恒清说什么也能不同意,就再缓兵之计把厂子组给别人经营。实在抵挡不过去了,他便遣散工人把厂子一关了事。1941年,日本人栽赃他和重庆方面做生意,把朱恒清抓了进去。两个星期后,妻子陆英娣托了关系用一包金条把他从牢里赎了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朱恒清,奋斗了一辈子,最后给子女留下了这幢带花园的洋房。 豪门深宅 我的兄弟姐妹 64岁那年,朱文琪生了一场大病,头发一下子白了,至今还断不了吃药,但是看起来精神却是很好的。每天傍晚她都习惯一个人骑自行车在附近兜兜,她从小就在湖南街道长大,只熟悉市中心区域,对杨浦、虹口却是非常陌生。 朱文琪兄弟姐妹一共5人,现在四妹朱文瑶住在她的隔壁,三弟住在二楼。兄妹的生母陆英娣在1960年去世了,后母谢慧芬已经100多岁,住在三楼。白天去拜访朱文琪,楼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声音。仿佛一座没了精气神的宅子。 1938年,朱文琪出生在苏州河边的老宅,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跟着全家逃难。“我原来叫朱翠珍,翠珍这名字是爷爷取的,虽然俗,但富贵。后来我人小不懂事,嫌翠珍这个名字俗气,后母(那时她还是家庭教师)就给我改了名字叫朱文琪,文琪是不俗了,但就是苦了一辈子。”朱文琪从小就不像大哥、三弟和五弟那样得到母亲和父亲的更多眷顾。“父母常常争吵,但有一件事他们很默契,就是对儿子的偏袒,所以我的出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喜悦。” 母亲陆英娣娘家当时在太湖边上有十几亩的上好土地和渔塘,出身在父亲之上。"但是她也是吃了一辈子的苦,亲戚常说,每次来,她不是下在厨房,就是忙在院里。"朱文琪把母亲的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照片上母亲丰润饱满,倒是有福气的样子,可事实偏不,"母亲是家里的第8个孩子,原来的7个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在了,所以外祖父母特别宠她,也把她宠出了一身倔脾气。"自记事起,父母的争吵声就经常在五兄妹中间响起,也许正因为这样,后母有了机会。 相比叙述朱文琪的家事,比叙述朱文琪的父亲生平让人觉得更难以下笔。豪门深宅中,故事的久远、深刻牵引着难以动笔,另一方面,故事中涉及的所有人除了父母都依然健在。朱文琪在叙述这段往事时,眼睛经常是湿润着的,我尽可能隐去一些,希望尽可能地不要伤害到这家人。但,对于后母,偏是逃不掉的核心故事。"后母谢慧芳原来是我们的家庭老师,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就想娶她做小。解放后,父亲只好找各种各样的由头发火,但是母亲的脾气也很倔。直到母亲去世后,1963年5月,后母进门了。为此父亲还订做了全套的红木家具,放进了他俩居住的三楼。"到1966年11月,朱家全部被扫地出门。谢慧芬也在12月与朱恒清划清界线离婚。 在那样的家庭里,儿子是负有沉重的家庭责任的。而女儿的作用似乎没有这么重要,相反地,对于这个家,如果没了物质上的追求和株连,注视的角度会相对清醒。"父亲的钱多得自己都搞不清楚,除了钢铁,父亲地产就有多处,当年他一口气就买下了宁波路204号的一座银行大楼,山西北路上的两条弄堂:怀德里、怡兴里,母亲悄悄告诉我,那是父亲买下来作为我和我四妹的嫁妆,还有苏州河边的老仓库等等。1950年,父亲从英国人手里买了位于杨树浦路的祥泰木行的码头,差不多同时,还从荣家手里买了500亩地,"朱文琪回忆说,"记得那年我三弟满月,爸爸在北京东路一家饭店摆了整整100桌,请客就吃了三天。" “小时候,我其实很男孩气,好打抱不平。家里老四也是个女孩,那时又小,老是被老三欺负,不是抓她头发,就是掐她胳膊,这个时候我总是冲过去保护她的,把他好好教训一下。” “'文革'期间小弟弟得了盲肠炎,需要86元医药费。看到这个数字我人也昏了。当时我先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元,我是40元,我们还有两个小孩要养活。那时多亏我单位的工会主席偷偷给了我20元。还有我的三弟和四妹,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江西,他们每个月都给我寄钱。新疆太空旷,三弟常常要赶100多里路才能给我汇上一次款。那时,每个月这几十元钱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982年,“文革”结束,谢慧芬与朱恒清复婚,朱文琪一家终于搬回了五原路。那种物是人非的苍凉,印证了这所房子。一进家门,顿时傻了。好好的一所房子,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家具都空了,固定在墙上的壁橱搬不走,但是抽屉也都被抽走了。原来花园的南部也被盖起了一栋六层的工房。 1986年,父亲朱恒清因病去世了,一代老上海钢铁大王得的并不是器质性疾病,却是营养不良。虽说是难以置信,其中牵扯的家族渊源又岂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财富人物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