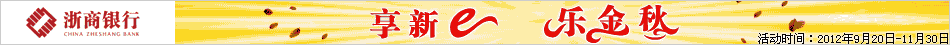再筑改革共识:建立利益表达和调整机制
春秋时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和发展史。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争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思想和理论界乃至实业界,都显示史无前例的关心和兴奋。
9月中旬,学者周志兴前往浙江北部的莫干山,参加一场被外界称之为“新莫干山会议”的研讨会。
28年前,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正是在此启幕。那次会议首开“官学互动”和“以文选人”的新思路,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会后形成的包括《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在内的7个研究报告受到决策层高度重视。
如今,“新莫干山会议”的举办方希望能“打捞历史,寻找改革新动力”。虽然与会者也提出了被称为五论的“推车论、一条腿论、起点公平论、价税财利联动论、政改关键论”,但作为国内思想与学术界的资深观察人士,周志兴对会议的成果评价并不高,“各有各的主张,没有一致的共识,具体的(改革)方案也离现实太远”。
在推进改革已成“最低共识”的当下,上述情况从一个切口折射出改革深化的难度:技术化的设计林林总总,却难掩各方的分歧;所有人都在谈论顶层设计,每人心中的顶层设计又各不相同;地方试验有得有失,类似当年小岗村式的改革突破口则还没有再现。
面对多元化思潮,如何整合多元社会,再建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未来社会的走向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
变形的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二战后居于主导思潮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这一困境,此前处于“边缘”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由此登堂入室。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倡导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单纯的经济思想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撒切尔和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在英国,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撒切尔政府启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在美国,里根政府为拯救长期滞胀的美国经济所采取的取消国家对经济干预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世界银行[微博]、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次会议提出的指导改革拉美经济的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华盛顿共识”伴随全球化进程一路东进,成为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支持者多、影响范围大的一股思潮。
中国经济1992年之后启动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从国企改革、发展民资、资本市场设立到加入WTO,随处可见在中国经济躯体上的投影。
这一时期,一些认同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经济学家逐渐走上主流舞台,他们所张扬的激发个体、企业活力从而带动整体社会活力的理念,影响了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知。
客观而言,鼓励民资和加入WTO,是推动中国经济20年来高速增长原动力中的两个要素。
但凡事皆有两面性,发生于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来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后,由于历史、经济、制度和文化基础的不同,其生长路径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异。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竞争,在一些领域,在“市场正义”的遮掩下演变为资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强势主导。新自由主义还渗透进医疗、住房和教育所在的社会领域。
政治学研究者萧功秦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滥用,让医院、基本住房和学校都变身为市场竞争主体。“无钱莫住院,只为富人盖房”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言论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结果则是药价、房价和学费暴涨,民生受损,影响了对改革的信心。
决策层意识到相关问题后,相继启动了深化和完善医改、房改等新措施,但市场对社会大范围侵入的后果至今未能彻底消除。
对新自由主义的致命一击当属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此之前,在新自由主义权势人物格林斯潘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渐取消对金融行业的政府管制,放任去除“枷锁”的金融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加速膨胀,并最终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主打民生牌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流地位终结。
来自发源地的反思与追问,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神像轰然崩塌。尽管诸如许小年[微博]等经济学家大呼:美国金融危机不是市场危机而是政府危机,但“这次危机对新自由主义信仰者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明确感觉到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一位学者在私下如此评价。
国家主义的兴起与反思
在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灾难电影《2012》中,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被设置在中国的喜马拉雅山顶上建造。电影里,当看到能容纳几十万人的巨大飞船时,一位美国的政府官员感叹道,“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能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伴随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悄然升起。
王绍光和胡鞍钢是国内最早关注国家能力建设的学者,主要借鉴西方回归国家学派的概念工具,对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进行研究。
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他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第一,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第二,调控能力,即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第三,合法化能力,即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经济地位的能力;第四,强制能力,即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威胁等方式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力。
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财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主张以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
学者许纪霖说,“在国家主义者们看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从古至今不是太强了,而实在是太弱了。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正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具有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国家主义的崭露头角是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非典高峰时期,中国各级党政机关显示出惊人的动员力量,深入到各基层社区,采取强制隔离、全民防范等措施,最终得以渡过难关。“一些学者,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对国家主义赞赏有加。”
国家主义在中国的闪亮登场,也恰恰是在2008年。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使国家财力大幅增强,与全球金融危机之中陷入衰退的传统西方强国形成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火炬等突发和重大事件,让国人的民族情绪异常高涨,原本就包含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顺势兴起。
有学者在汶川地震后抗震救灾重建的全过程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大家多谈“个人”,90年代人们谈论的关键词是“阶层”,而这几年则转移到了“国家”。从大众的文化消费角度大体可以印证这种观察,这一时期,民众议论的还包括央视的纪录片《大国崛起》。
此后,随着中国GDP连续超越德国和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国家主义的优势会被时常提及。
有学者甚至论证指出,正是国家的中性色彩和强大能力,或者说是“自主的理性”,使其能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不断将中国推向前进。
中国模式受到关注。围绕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其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中外学界展开了一场耗时长久的争论。
赞成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同时,国家的“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崛起。
非赞同者指出,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乃至生产成本的行政管制,固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是这种不是依靠效率提高、而是依靠大量投入资源支持的人为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国家的特点是上令下达,让国家配置市场资源与市场创新的需求是很难调和的矛盾。
这场争论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冲击,一些在高速增长中被掩盖的矛盾逐渐显现,使得国家主义的支持者也开始陷入反思。
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使得中央与地方在分税制上的矛盾逐渐凸显,财政收入增速大大高于民众收入增长水平;GDP增长主义盛行导致地方政府无止境地投资拉动经济,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已达临界点。
人民日报社的评论明确提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似乎也标志着国家主义在中国步入反思期。
走向共识
胡锦涛总书记“7·23讲话”被视为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一次重要理论吹风。在这次讲话中,胡锦涛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基本有这样一个观点,执政党在实践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吸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越来越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实际相结合,越来越趋于务实,越来越趋于凝聚共识。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经济起飞20年以后,中国逐渐进入分层社会,社会结构的分层必然导致利益分化,各阶层对于未来中国如何走,都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自己的想法,多种治国思潮必然产生。
周志兴则表示,表面上看,社会思潮只是观念差异,但归根结底反映的还是利益调整和力量消长。这种利益调整不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增量调整,而很有可能意味着某些部门的权力会变小,利益会减少,某些群体的权利诉求会更高。
“现在的问题是,各方观点都有极化倾向,需要弥合共识裂度。不仅仅是引导和控制社会思潮,而是如何建立合理有致的利益表达和调整的机制。”
他认为,应对形象色色的社会思潮,应该更多扶持中间改良力量,推进各种对话,这种对话的目的一是建立对话规则和行动底线——包括允许人说话的底线、法治的底线、非暴力的底线等;二是寻求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如反腐败的共识,建立市场经济的共识、依法治国的共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共识等,并将这些共识上升到体制层面,以法律和制度安排的方式加以巩固。
同时,坚持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满足民众利益的合理诉求,让民众参与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多元化,特别需要发展创新能力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时,体制的惰性却约束了改革的动力。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人们就会被各种思潮所吸引,接着就会进入左右之间的社会拉锯冲突。
萧功秦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中道理性的原则,在现行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
近期,中央政府连续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明确表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座谈会表示,下一步要深化财税、企业、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多项改革措施。
萧功秦就此谈到,连续改革措施的出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做几件让民众高兴和提振信心的事,当然推进更大程度的改革还需时日,因为“合理的改革理论一定是全民智慧的结晶”。萧认为,在多元化思潮并起的背景下设计改革一定要制定终极目标,比如强国家与强社会的组合。“没有这个终极目标,改革的试错极易被利益集团俘获为自身盈利的工具,社会期待的顶层设计也很可能流为乌托邦式的空想。”
蔡霞认为,执政党要应对思潮多元化的变化,就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革,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她看来,执政党的改革方向,首先是整合多元社会的共识,在这基础上根据中国的传统、国情与现实,进一步发展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聚最大共识,进而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与政府,同时做好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准备。
一位决策层的幕僚人士表示,利益与观点多元化的情况下,改革的最终方向一定是沿着合力线的方向前进,是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单是愿景是什么,而是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