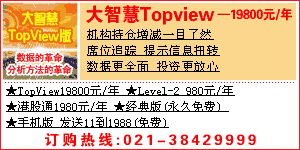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郝建:为中国电影看病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8日 11:07 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 个人身份的定位 郝建这些年来不停笑骂中国电影。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的教授,主业是搞电影理论研究的。电影理论经常被看作是一个自足的小宇宙,是与某部具体影片没有多大关系的自足的语言系统,郝建则经常能对新的电影现象及时进行回应,使得这些电影成为更大的话题,也动员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争论里来。对此,郝建有一种自觉意识,他觉得电影理论“经由评论是可以促进电影艺术形态的变化发展的,它可以让研究者和创作者对电影的形式体系和当下活跃的文本更为自觉。” 虽然一些导演对于电影评论并不感兴趣,声称自己不会受它们的影响,但事实上,却有些导演根据这些呼声来调整自己此后的创作,评论者与创作者一起塑造着中国电影的文化,只是这个经由文字的交流的效果经常被掩盖掉了。 电影导演多是出产自电影学院,郝建没有因此而为校友避讳,他批评电影的文章经常使他显得不近人情。他这些年一直在批评一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作品,不久前张艺谋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翻译,一个女生前来应聘,当女生报称自己是电影学系的学生时,张艺谋马上反应——就是那个天天有老师来骂我的那个系啊! 骂他的老师,以郝建最为有名。当然他并不只是为了骂而骂,有时候骂里有一种自我娱乐的成分,一种语言快感的追求,但也有问题意识和建设性。在第五代刚起步的时候,他也曾赞美第五代在形式和个性张扬方面的革命性。他说,他的批评其实是针对作品而来的,主要是电影中包含着的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成分。 郝建搞过电影创作,对于电影中的形式比较敏感。他说他看电影像听音乐一样,能够分析出其中的结构关系是否和谐。郝建编剧的《紧急迫降》曾获得过华表奖,而且他熟悉电影剪辑等制作程序,所以能够对一部电影进行细腻的技术分析。但是,电影对于郝建来说,主要还是帮他找到了一个比较及时的“公共话题”。目前的影评人有很多种,有一些是年轻人在报纸上写的一些感性的评价文章,有的是比较学术的纯粹技术分析,也有一些是自由知识分子以电影为话题,作为公共交流的一个契机和场合……郝介于后两者之间,并主要是自觉以电影为公共话题展开与社会的对话。 影评人的价值和作用亦有所不同。有的影评主要是作为产品介绍,是电影产业链中的一环;还有一种注重的是电影作为时代精神的构成,注重研究电影在社会上传播时的文化效应。郝的着力点则在后者。 郝建的另外一个比较自觉的工作定位,则是要进行更为广泛的文化批评,他涉及的领域比较杂,他研究过电视剧,写过各种公共艺术活动比如音乐会、实验话剧的文化分析。 论“为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总结他这些年的评论,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批评第五代导演的几位主将们不约而同的犬儒主义。第五代导演胡玫的《雍正王朝》的歌词里有一句 “天下万苦人最苦”,他从中听出来的是“天下最苦,皇帝最苦”的声音。他在张艺谋的《英雄》里看到了“荆柯护秦王”的一种犬儒主义和反动意识,他把《水浒传》里的侠义只是看成了可怕的 “流窜做案”。最近又批评姜文的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分析了姜文在电影叙事上表现出来的表面的自由和内心的极端不自由,这同导演本人对文革的处理态度有关系。 他是怎么批评《太阳照常升起》的?他首先指出这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文本,电影其实以商业片来进行操作,但因为蔑视观众而缺乏与观众的对话意识。更为关键的是,电影中关于文革的叙事使人感觉到了作者拣选记忆时的避重就轻和逃避—— “作者假装看不到凌驾于我们生活之上的老大哥,却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谁都不理会,谁都不惧的老大哥,这是一种十分犬儒主义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形而下的感官享乐当作先锋突破,如果我们在简单的话语放纵中自鸣得意,我们把这种形而下的感官崇拜当作形而上的思想探寻,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影片故意改写历史,它把一个黑暗年代涂抹成一个为鲜花盛开的村庄,把简单的个人独白当作必须让观众去理解的深刻思想,这就是把犬儒主义当作英雄主义。” 郝建时常以一句话来形容一些作者的思想表情——“为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他说这句话时,针对的是那些反商业和全球化的学者们。其实,这句话既可以针对某些导演在创作电影时似乎是无意识下犯的错误,也可以针对整个学术界的另外一些现象。比如一些明星学者经常制造一些观点,这些观点看起来十分的有锋芒也十分的真诚,比如有些学者的民族主义,比如“修缮自我,不要抱怨外在环境”,看起来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思想表达,其实是经过了周详的利益考虑后的发言。那些发言看起来头头是道,有时候甚至会让人义愤填膺,显得颇有正义感,其实是屁股决定大脑,只是为了做给权威看的“为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这并不是认识能力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认识的问题。这是一种猥琐人格的矫情,其原因是其内心缺乏社会良心和一份真正的对于真理的敬畏。也许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但至少要有一个自我 自觉的意识,惟其如此,才不至于让自己那么严肃地撒谎,甚至自己把自己都骗过了。 电影叙事活动如何影响社会? 郝建的影评与一些年轻人的影评不同,他写影评有更多历史经验的参与,有比较充足的历史感,比如他对于文革的话语十分敏感,总能从一些作品中看到文革的后遗症,对于对那段历史缺少认识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从电影中诊断出这样的话语存在的。郝建认为文革话语对第五代乃至姜文这样第五代之后的人有着非常深的影响,但人们也许会说,电影不过是一种娱乐,或者顶多是艺术,何必让他们有那么多的负载呢,这会不会是一种泛政治化? 郝建认为若他们是单纯的娱乐,他会以单纯的娱乐来对待。事实上郝建一直在研究的领域是暴力美学,着重于研究一种纯粹的形式趣味,他是欣赏暴力美学的,比如他在很早就四处推广昆汀·塔伦蒂诺和吴宇森等导演的暴力场景的设计,但他也认为那种暴力美学需要一种良好社会体制和良好的文化空间来做底子。 他不反对暴力美学,却反对“美学暴力”。什么是美学暴力?有一些导演在一些叙事场景中并没有暴力的表象,其强硬灌输价值观的诉求却是另外一种隐藏着的暴力行径。郝建认为,电影是一个与社会的对话活动。电影叙事活动与社会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琐细,不易觉察,却并不是不重要的。 看电影能够使人的经验得以发展和开阔,时代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塑造。列宁曾将电影看成是所有文化形式中最为重要的艺术种类,他觉得电影是最能号召和影响大众的。郝建在谈类型电影的时候讲到,类型电影的叙事活动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和普遍的社会精神活动具有互动性和交流性,而现代人类的理性也正是在这种动态的、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他相信哈贝马斯说的,道德是在公共交往的过程中确立下来的,而非只属于个人心灵的、先验的。看电影、评电影自然都是这个社会交往的一个部分。 看来他并不认同商业电影的纯粹性,这也就是他那么注重侦察电影透发出的错误价值观和以写影评来平衡其社会效应的一个动因。 呼吁娱乐,反对“硬作狂欢” 郝建是国内类型电影的主要研究者,而且也许是最早的。类型电影在美国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其研究专著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郝在1988年发表了研究类型电影的文章,背景就是由于当时娱乐片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潮流,类型电影可以为娱乐片提供一个比较适合操作的方法。 郝建也是最早呼吁商业娱乐电影的学者之一。商业电影往往被看作缺乏思想性、平庸、体现粗浅的大众水平。但郝建呼吁商业电影,也许有着另外一层的考虑,他认为呼吁商业和娱乐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思想。他对于周星驰的吹捧也是不遗余力的,据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等电影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次放映后,被电影学院的师生一起抬起来的。郝建也是其中的力量之一。 在国外的商业电影中,类型电影占有最大的比例,而且创造类型电影对于投资家来说,是商业风险相对较少的。类型电影在国内经常被看作是模式化的、浅薄的,但郝建却赞美类型电影,因为类型电影里所包含的价值观和形式趣味是平民化的,是在与平民观赏趣味的交流中被固定并继续发展着的。郝建这些年对于类型电影的推崇和商业电影的鼓吹,有很大一部分是看重了商业电影对于公民社会建设的作用。 郝建认为中国的类型片在解放前是比较发达的,到了80年代以后,又逐渐有了新的类型电影的出现,但到了90年代,商业类型片被主旋律电影所领导和抑制。现在类型片还在艰难的起步中。 他呼吁商业娱乐电影,但他反对硬作的狂欢,他出了一本书名叫《硬作狂欢》,分析那些看起来十分HIGH的欢乐表情其实是多么的虚伪,因为其内里空洞。有许多学者专门撰文批评中国的商业文化和由此生发出来的大众文化,以之为批评的对象和靶心,并称之为“大众文化的狂欢”。郝建指出说这个是 “商业狂欢”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商业环境,那种商业文化的平民化的大狂欢在中国并未真正出现过。 出现过的,只是一些硬作的狂欢,是那些“把规定设计好的趣味当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成真的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这种被限制的狂欢早就成为一种听取将令以后训练有素的美学齐步走……” 正如他批评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所说的:“如果我们把经过计划、规定的笑声当作真正的欢乐,把指令导向下的硬做狂欢当作是真正的纵酒放歌,这就是一种心知肚明却照旧服从、归顺的犬儒主义。” 他反感的是中国电影中出现的集体主义的团体操般的美学风格,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各种电视剧和电影,包括各类晚会的开幕式与主持者的情绪煽动,其实都因为过多的控制和过滤而逐渐丧失了真正活泼的精神,那些繁荣很少是真正体现大众广场上的笑声的,而只是一种罐装笑声,或者说强制的煽情。这也许正是中国电影电视的叙事让人觉得不自在的重要原因所在,因为它有着各种限制,不能彻底的自发自动,也就无法真正尊重接受者的趣味。 访谈 问:跟许多做电影理论的人不一样,你写的东西好像比较杂,除了电影评论,电视剧评论、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艺术设计这些你都评说过,你的文集《硬作狂欢》里还有一篇讲听音乐会的行为修养问题,这对一个学者会不会太分心而影响专业度? 郝: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念本科时我写的第一篇学生板报文章是讲西方现代派美术……我写过两个电影剧本,上海电影厂拍摄的《紧急迫降》和紫禁城影业公司拍摄的《危情雪夜》,电视剧做的就多了,播出的有 《大屋的丫环们》、《真空爱情记录》、《汽车城》、《冲出绝境》,对了,李扬《盲山》的拐卖妇女题材我在 2002年也写过,当然,我写电视剧必须要求写出光明来,播出时叫《又见花儿开》。 问:你是理论教师,为什么要写这些商业性的剧本? 郝:写剧本挣钱多啊,这对我的生活和人的状态有很大决定性。因为我手头还不算窘迫,写理论和评论就爱写什么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的假想读者只有那些买报纸和杂志的人,我从来不会从影视公司拿钱写东西。当然,去开会,吃人家的酒席是有的,钟惦斐老师跟我们开玩笑地说过,吃人家的饭吃得嘴油油的哪里还说得出真话。 问:那你觉得你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郝:写评论和创作都是在寻求一种语言表达的美感,我的兴趣在于探索文字的结构和肌理,我在这文字的编织、推敲、紧缩和飞扬中得到一种快感。另一种快感是来自于跟其他人、跟社会的交流,或者简单说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吧,我有文化批评的情结,又有比较清醒地与各种意识形态和艺术趣味进行对话的愿望。但是我在写作上,在话语上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在向一种非常平实的明白的话语上进行转换,这个是我有意识做的。如果说文本上的标杆吧,我觉得这个要说到王小波和王朔——主要是王小波,这是我自觉追求的,包括我写了文章请一些朋友看,我追求讲大白话。 问:从你的评论和创作来看,你一直把大陆的大众文化作为积极元素来评价,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的许多观点是不是有所改变? 郝:对大众文化我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评价,我不满意大陆一些挺时髦的观点,简单地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庸俗甚至低俗的东西,当作是已经成为权威文化的东西来加以警惕和抵制。在这方面,我对当下语境的总体估计没有变,大的思路、价值观也没有改变。 问:近几年你好像对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有许多批判,主要观点是什么? 郝:对于作为创作者的第五代导演,我从来没有在整体上批评他们,我试图从具体作品来剖析我们的文化心理,我们当下社会的文化走向和一些作品的价值取向——从第五代导演后来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文化创作、文化产品、文化人的心理结构与中国市民社会和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具体说到第五代导演,我对他们在新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较喜欢。你去查《文汇电影时报》,1992年我有一篇《扛着累累硕果的张艺谋》,我对于那时的张艺谋的创作,不管是从创作还是文化心理上,都是很欣赏的张艺谋的 《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表现出来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对个性解放的呼唤。作品里有对人的个体选择的肯定,在电影语言形式上也有一种强烈的创新冲动,比如《黄土地》呈现了导演的语言突破能力,这里面有他们个体力量的一个爆发。一直到今天来看,这些东西还是有它的积极价值。 问:你对张艺谋的评价有一个转变,好像是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一直到他拍摄大片。 郝:对,我对张艺谋的作品有一个简单的划线,一直到他的 《有话好好说》,我都很喜欢。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张艺谋的作品和在报纸电视上的社会表态都出现向主导性的话语转移的趋势。陈凯歌呢,他的电影和权威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一直是肯定和追寻人的个体自由,但是他的心理价值观上集体主义的内容更多些。他的《大阅兵》就有向集体主义价值观靠拢的倾向,当然要细说不那么简单,可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思,有时是在批判和对抗中的臣服……不是说他要讨好谁啊,献媚谁啊,他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这样做,我想研究的是他在文化心理上与权威的关系,或者在美学上他和权威话语、流行的艺术观念的关系。对于权威的一种崇拜和不自觉的一种受虐心理,我的分析是他们青春期既当红卫兵又受到伤害的心理后遗症。比如说从《大阅兵》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那里面似乎有对整体、纪律、威严的队伍和空旷广场上整齐步伐的力量的表现,当然这是对抗还是不自觉的臣服和崇拜还有具体读解文本来分析。从我的价值观来看,我对这种过分整体性的、从集体性主义的价值观去塑造人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在中国当代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个体的觉醒、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是一些负面的价值观。 问:其实你是要分析电影中所呈现的集体无意识,包括你前段时间对于姜文的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的批评,他们的电影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呈现给你提供了一个话题,也许你并不仅仅针对某个具体人,其实是把他们的作品看为整个社会的病历。 郝:对,他们的作品只不过给我跟社会对话找到一个契机,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标本。他们的作品是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而存在的。我在寻求电影的形式快感的同时也在分析他们的电影创作背后的文化心理,比如说《太阳照常升起》是一种非常暴力的话语,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的话语。作者的创作心态很有趣,就好像一个伟人在朗诵自己的诗篇,所以在美学上和在艺术理念上他用了大量的比较强力表达意念的杂耍蒙太奇,所以他有大量对观众的直接喊话,大量的非叙事性的话语,导演时常对观众自言自语,比如他让疯妈说:“你可以说你不懂,但你不能否认你看见了。”这如果是自己写的诗歌拿到博客或者文学杂志上去发或许很美丽,但在讲究对话、交流的商业电影中是很强势的,是犯规的。 问:有很多观点持有者,可能会觉得你对大众文化、商业性这一块过于乐观了。 郝:我是从提倡文化的丰富性、提倡我们民族的艺术活力和创造力的角度来抨击文革意识形态的。大陆是趣味饥渴、幽默饥渴、故事饥渴,所以看到出了一个 《疯狂的石头》,整个大陆文化界、评论界就欢呼雀跃。当然,有的人认为趣味的单一化和被压制是由于资本的原因,由于商业社会的原因,由于金钱的原因;我看到的正相反,商业交换这一套机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天地。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提供的艺术就是在金钱当中交换的,就是在交换中完成的创造,你说是铜臭也好,鲜花就是和金钱的闪光一道焕发出它的魅力的。我们要仔细具体分析,到底是全球化、市场经济秩序,还是管理上的体制性制约、公平规则的缺失压抑了电影的创作。 问:你一直在研究类型电影,类型片的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对于电影商人来说,操作类型电影的商业风险是比较小的。 郝:它是一种约定俗成,是对于观众的趣味、心理,还有伦理、价值的一种尊重。最重要的,它的规范不是那几个人单向设计的,是在跟观众的反复交流中自然形成的,这与哈贝马斯说的交往中建立的理性、交往的合法性完全符合。最近我看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他那里面是不讲故事的,我就顺着他的趣味反过来思考,电影可不可以不讲故事?为什么电影要讲故事?你看好莱坞的商业电影主要是讲故事,而且一定要把故事讲好。一定要讲故事,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它是一种对话。讲故事不是一种宣告性的话语,不是一种独断性的话语,讲故事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对话并且在发扬一种对话中的理性。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新浪财经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