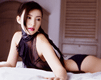|
贸易摩擦进入战略性法务攻击,应诉之路更加艰难
王海镇
近日我国原料药四大巨头正遭遇来自美国企业的《反托拉斯法》提诉,这说明我企业在经历了反倾销提诉的初步洗礼后,已突入国际贸易摩擦核心区——战略性法务攻击(利用
各种不同法规同时发起攻击)。由于应诉此种攻击的复杂和艰巨程度,远非反倾销应诉所能比,这对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的中国企业而言,将是一场鏖战。但纵观世界500强,无一不经历过《反托拉斯法》诉讼的洗礼,虽然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一天来得早了点,但既然无法回避,就必须积极寻求对策。
日前华北制药和江山制药均向媒体证实:其已与石家庄制药和东北制药一道,分别收到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根据《海牙公约》规定送达的传票,作为原告的美国两家公司诉称;自2001年12月起,被告公司联合操控出口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维生素C(以下简称VC)的价格和数量,触犯了美国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垄断法》。诉状还称:2001年12月,中国6家Vc企业在中国医保商会西药部组织的会议中,达成Vc出口数量和价格协议,故意控制产量,造成全球Vc市场供不应求局面,从而抬高产品价格,谋求高额利润,致使原告方因“支付了高于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购买价格而蒙受损失”。
面对美国法院突如其来的传票和首次遭遇的《反托拉斯法》诉讼,我涉案企业颇感困惑,甚至有涉案企业在发布的公告中,也称“我企业被诉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原告还向法院要求索取3倍不明损害赔偿及其他辅助赔偿,不明白对方提诉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统计,2004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VC,占中国VC出口总量的31%,平均离岸价为每公斤4.57美元,低于全球平均离岸价4.63美元,中国企业并不存在高价垄断市场行为”。
看来我企业并未搞清被诉的真正理由是什么。
应该说我涉案企业被诉违反的并不是《反垄断法》,因为美国并没有《反垄断法》,只有《反托拉斯法》,因此被告的罪名也就不是什么“垄断行为”。
《反托拉斯法》是指由《谢尔曼法》、《克莱伊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相关法律构成的一个法规群,这些法律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行为。
就本案被诉的具体情形来看,原告诉称是“操控价格与数量的价格联盟”,故原告的依据应该是《谢尔曼法》第1条,即俗称“禁止卡特尔”条款。因为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构成垄断行为的首要条件是:被告必须有“垄断”特定市场的地位,或对特定市场有支配力。同时垄断指控往往适用于企业的单独行为(如微软被诉事件)。而目前我企业远未达到控制国际VC市场的地位,涉案企业也多达4家,因此谈不上垄断。
但就《反托拉斯法》对卡特尔行为的解释来看,其并不需要行为者有垄断地位的要件,行为和涉案企业的市场份额也毫无关系,原告只要证明处于竞争关系的同行业者之间(被告),达成或存在某种限制竞争的共谋和事实,并因此限制了特定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即构成违法,哪怕是规模再小的企业,也要被追究违法责任。
如此看来,本案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企业是否有垄断行为,也不在于你的价格是否合理,而是在于你是否有“人为固定价格”的行为。一旦法院认定违法行为成立,根据《克莱伊顿法》第4条,被告将面临3倍赔偿责任。
制定于1890年的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明确规定:所有限制州际、与外国贸易或商业的契约、托拉斯及其他形式的结合或共谋,均属违法行为,缔结违法契约或共谋者以重罪论处;罪行确定后,法院可酌情对法人处100万美元以下罚款,个人可处10万美元以下罚款或3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罚。2004年以后对企业和个人的罚款,已分别上升至1亿美元和100万美元,刑期也飙升至10年。
在1927年特兰顿.波特雷斯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参与价格卡特尔的涉案企业,能够就商品的市场价格达成协定,意味着这些企业聚合在一起可以支配市场,自由操纵市场价格,这样形成的价格毫无合理性可言,并留下一句名言;“如此形成的价格,即使在今天有其合理性,随着经济和商业条件的变化,明天就会变得不合理”。
法院还在此判决中,明确了《反托拉斯法》的宗旨:该法的立法目的,不在于产品价格是否合理,生产数量能否扩大,而在于各企业对产品价格和生产数量的“自由意志决定”是否得到保障,任何人为影响产品价格的行为,都不能容忍,应视为违法。
1940年的索考尼事件,联邦最高法院又确立了对卡特尔事件适用“当然违法”的原则,即参加(卡特尔)协定的企业,无论其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力,只要人为操纵了价格,即意味着在其影响范围之内,自由的市场机制已受到人为干涉,其行为本身应视为违法。
此后,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诉讼中,对各类卡特尔行为(包括限制价格、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卡特尔行为等),只要具备行为外观特征,原告无须证明实际损害发生,法院即可认定违法。
由此可见,本案的关键在于我被诉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合谋”操控市场价格的事实。
从相关报道来看,我涉案企业对原告指控的对VC的销售价格进行磋商一事并未否认,虽然中国医保商会相关负责人强调会议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状况下举行,但这也恰恰证明“合谋”的事实存在,至于会议内容对法庭而言已不重要,这对我企业是个不利。
2002年7月美国第四联邦巡回法院审理的“国际橡胶制品卡特尔事件”,涉案的马来西亚、泰国等企业在吉隆坡、科伦坡、巴厘岛等地定期会晤的过程,即被法庭陪审团认定存在“合谋”。
从这些分析来看,我涉案企业要否认存在“合谋”事实,并非易事。从《反托拉斯法》的相关案例来看,涉案企业败诉的几率也不低。
但笔者注意到相关涉案企业在发布的公告中提到:“收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里斯托尔县高级法院根据《海牙公约》送达的传票、诉状等相关诉讼文件。”从文件送达方式来看,本案应属《反托拉斯法》诉讼中最为敏感的域外适用案件。若如此,我企业应从《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的相关法理来考虑应诉战略。
根据《克莱伊顿法》第12条后半段规定:《反托拉斯法》诉讼的相关司法文书,可在当事方所在地(注册地)或现在地(日常活动场所)送达。
如果我涉案企业在美国有子公司或分公司,按照美国法院的一贯做法,法院会直接通过这些关联企业送达法律文书,而不会根据《海牙公约》来送达。由此可以断定,此案属《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案件,即意味着我企业并没有直接在美国销售产品,被诉的“合谋”行为也完全发生在中国,如按国际法的主权管辖原则,美国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故我企业可提出管辖权异议甚至拒绝出庭,但结果将以我企业退出美国市场为代价。
如我企业拒绝出庭,即使美国法院最终做出缺席判决,也无法在我法院请求执行。因为美方对本案管辖权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以及3倍赔偿的要求,我法院无法执行(日本、德国、英国等都有拒绝3倍赔偿的先例)。
但是,考虑到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规模和影响,我企业可能因不愿放弃这一市场而被迫应诉,此时最重要的是选择好应诉方向。
据报道,此次我被诉企业曾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反倾销调查,若属实的话,可考虑以此为抗辩理由,但必须提供有效证据,包括美国商务部的信函、通知或其它资料。由于该案属域外适用案,美方原告负有对“实际损害发生”的举证责任,而且这种损害必须是“实质性”的。
所谓“实质性”,是指美国该产品市场由于中国产品的价格变动,造成大多数客户实际利益受到损害。但从2004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VC占中国VC出口总量的31%、平均离岸价为每公斤4.57美元、低于全球平均离岸价4.63美元这一事实来看,原告在美国市场受到的影响有限,故原告的举证并非易事,只要我涉案企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应诉战略上把握整体辩护和庭审方向,强调与反倾销措施的关系,在战术上严格确认、仔细研究双方的每一个证据,把握好每一个程序,包括应对陪审团的对策(此案很有可能采用陪审形式),就有胜诉可能。但应诉所需的时间可能是漫长的,企业应有充分准备。
从目前涉案企业既有说“收到来自州法院的传票”,也有说“收到来自州联邦法院的传票”来看,我涉案企业对此案的研究还不够,因为美国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适用法律和程序都是不同的,美国既有联邦《反托拉斯法》,也有各州自己的《反托拉斯法》,如将二者混为一谈,后果不堪设想。
我企业在应诉过程中,还必须考虑此案的扩散效应。
美国司法部和欧盟委员会早在1991年就签订了《反托拉斯法》的司法《合作协议》,与日本政府也在1999年10月签订了同样内容的《协议》,故有关此次诉讼的相关信息,会被这些国家相互交流。这对处于同样忧虑中国产品进口大增的欧盟和其他国家来说,有可能成为对中国企业挑起《竞争法》诉讼的一大证据。
欧盟《竞争法》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还有欧盟各成员国的《竞争法》,故又被称为二元化《竞争法》,这些《竞争法》也有域外适用前例(如德国),因此我企业在应诉过程中,对所有相关资料、证据使用、抗辩理由构筑等,都要慎重考虑。
从国际贸易摩擦的历史来看,在经历了反倾销、反补贴、紧急保障措施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势必会遭遇进口国《反托拉斯法》(竞争法)、《产品责任法》、《知识产权法》等的攻击,甚至出现各种不同法律同时提诉的局面,提诉方的目的只有一个:驱逐或拖垮竞争企业。如以松下、东芝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1970年代初的Zenith案件,就曾遭到美国企业的立体法务攻击,涉及的法律包括美国1916年的《反倾销法》、《威尔逊关税法》第73条、《谢尔曼法》第1~2条、《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罗伯逊~伯特曼法》第2条及《克莱伊顿法》第7条和巨额的3倍赔偿索求,被罚金额高达12亿美元。此案自1970年开始,直到1986年才以美方败诉告终。虽然日本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正是因为有了此类复杂诉讼的经历,今天的日本才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法务专家,并培养出大批精通国际法务的企业人才。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对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格局的影响非常大。但与此影响不对称的是,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竞争法》方面的立法明显滞后,这对我市场、我企业的成长和成熟很不利。政府只有尽快制订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才能在问题面前调动政府、企业、学术界的力量共同应对,才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各种有效保障。
资料连接:
何为《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
《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是指即使是由外国人(或企业)完全在美国国外实施的行为(如价格协定、拒绝交易、市场划分等反竞争行为),当这种行为影响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时,在一定条件下(拥有程序管辖权)对该行为适用美国《反托拉斯法》予以追究。
但由于这种追究与《国际法》主权管辖原则(属地主义)相矛盾,国际社会乃至国际法学界,至今对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都表示反对。但美国却以“维护美国乃至世界公平竞争秩序”为由将其适用至今。
1945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的伦纳特.汉顿法官在审理阿尔科案件中,便对“涉案企业均为外国企业,本案协定也是在国外(瑞士)签订,故美国法院无管辖权”的抗辩做出如下判决:即使外国企业发生在国外的行为,如该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并且这个行为是有意识进行,而且在美国产生了效果,美国法院对该事件就拥有管辖权。
这便是闻名世界的“效果理论”,阿尔科案也由此成为《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的首例。
1982年美国《反托拉斯改善法》对该理论进行了修订,使其成为美国法律的明文规定。
根据该规定:发生在国外的行为,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出口机会)、进口贸易(价格限制)及国内贸易(消费者包括购买方利益)产生直接或实质性、且是可以预料的效果时,将受到《反托拉斯法》的追诉。
自该法生效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出现了财政与贸易的巨额双赤字,《反托拉斯法》提诉已出现异常激增之势,为扩大其射程范围和威慑,《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也异常活跃,事实上已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