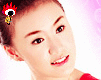中国科技财富:煤价飙升 外资撤离中国电力市场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4月13日 12:23 中国科技财富 | |||||||||
|
2005年初,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雪花纷飞,天气相当寒冷,这与很早就预报的暖冬天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与这种反差相映成趣的是西门子公司逐步撤离目前正热得发烫的中国发电市场的行动。1月5日西门子公司向外界证实,去年年末,该公司与另外一家外资电力公司——德国汉堡电力公司一起出售了在河北邯峰电厂共达40%的股份,收购者为中国华能集团和中信集团公司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出售邯峰电厂只是其逐步淡出中国发电市场的第一步,西门子目前在中国另外16座发电厂中拥有股份,而这些股份都在出售之列,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的是山东日照电厂。 不久前,西门子集团公关部负责人王君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投资领域不会再放在发电上,而是要集中到发电设备上。”这样的回答一方面印证了西门子将逐渐淡出中国发电市场的说法,一方面又让人感到隐约其词,似有难言之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电力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的现实,这种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其实,西门子撤出中国发电市场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是新一轮外资撤离中国电力市场热潮的延续。2003年开始,很多外资企业都逐步放弃了在中国经营了约十年的电厂股份,纷纷收拾行囊,选择了离开。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随手拈来,便有不下十起。 2004年3月,美国电力公司出售了河南南阳浦山电厂70%的股份。再往前,2003年3月,美国赛德能源公司将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份转让,并陆续出售了广东东莞厚街电厂、河北唐山热电和湖北蒲圻赛德发电有限公司的股份。此外,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撤出了广西来宾电厂B厂项目的40%股份,全球第三大能源巨头美国迈朗公司出售了它在山东国电和广东沙角一电厂的股份等等。 中国卷起红地毯? 2004年的外资集中撤离实际上是外资撤离中国电力市场的第二波浪潮,而第一波撤离潮发生在2000—2001年。关于2000年开始的第一次外资撤离浪潮的原因,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即原有的优厚协议被取消,外资发电企业利润率得不到保证,所以选择离开。 外资电力公司投资中国,始于1980年代末期。当时中国电力需求增长很快,而中国又急需大量的电力建设资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鼓励和吸引外来资本进入中国的发电领域,开出了年固定回报率为15%到20%的优厚条件。 当时的地方政府,如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开风气之先,许以外方固定的回报承诺,比如在多少年内的上网电价为多少等,并以合同的形式标明,以降低外方的风险,换取外方的投资。 此风一开,世界上众多大型电力投资商纷纷来到中国寻求机会。据中国电力联合会前秘书长陈望祥回忆,大约10年间,有三四十家外资公司来中国投资建设电厂,装机容量总计约2700万千瓦,形成了一波外资电力企业投资中国的热潮。 到1997年,外资占我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经达到14.5%,成为历史高点。 然而,外资电力的好梦在1999年惊醒了。当时,中国电力进行大重组,供应出现了过剩。在这期间,对外资承诺的固定回报已不符合当时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中国逐渐取消固定回报政策,导致外资企业纷纷离场。外资的纷纷离场相应地也使外资占我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最高时候的14.5%,迅速下降到了2002年的7.5%。 对此,许多投资商指责中方没有信守保证固定回报的承诺,很多外国媒体更是添油加醋地将此描述为中国开始对外资电力企业收起红地毯。中国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设定固定回报率有违公平,如今国家发改委在审批一些外资电力建设项目时明确要求,任何地方不得对外资企业承诺固定回报率。 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业内的专家也表示,承诺固定的回报率等保证外资电力企业利润的做法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十分罕见的,这等于说只要外资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建成电厂后,无论放在哪里,每年就可以得到投资额约20%的回报,这显然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而且对国内电厂来说,也的确有失公允。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只是让外资企业跟国内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谈不上是对外资电厂卷起红地毯。 而一位国内发电企业的高层也表示,即使外资现在撤出,也占了很大的便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当我们国内的发电企业为了给自己的发电找个买主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他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坐拥20%的利润,这么多年下来,投资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 虽然经过了第一轮撤出浪潮,但仍然有一部分外资企业对中国的电力发展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凭借良好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实现盈利,所以仍然坚守阵地留了下来。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外资电力企业的投资存量大约还有1200亿人民币左右的规模。 而2004年,这些留下来的外资电力迎来了第二波撤资潮,这对于仍然保存下来的1200亿的电力外资会造成多大的冲击,目前还很难估计。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外资的二次撤离,一些专家给出了解释:由于煤炭价格从2003年开始一路飙升,很多外资电力企业由于承受不了煤价上涨而带来的发电成本增加,利润得不到保证,而最终决定退出中国电力市场。 煤价是把刀 煤价的上涨对火电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的打击的确十分明显。一些外资电力企业表示,煤价的不断上涨就象是一把锋利的钢刀,在不断削减他们的利润。在采访太平洋顶峰电力公司的时候,公司CEO罗伯特·安德森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近两年中国煤价走势图,并在2003年11月处画了一个大圈,图表显示此时煤价为240元/吨。而从2003年11月份到2004年8月份,煤价一直在上涨。煤炭价每吨上涨了170元,从百分比来讲就是50%。从2004年8月后,煤炭价格仍然在高位运行,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 “我们是较早来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跟我们一起来的外资同仁,已经有近40家收拾行装离开了。”太平洋顶峰电力公司CEO罗伯特一脸无奈。 太平洋顶峰是在中国排名前五位的一家外资电力公司,出资方为世界500强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和世界银行等。到2004年底,太平洋顶峰一共在中国投资了7个热电联供企业,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总投资额达到了20亿元人民币。之前的几年,太平洋顶峰在中国的热电联产企业的运营一直处于盈利的状态。 然而,太平洋顶峰的七家电厂在2004年出现了四家亏损、三家电厂微利的状况,总体上核算,2004年该公司将出现亏损。据罗伯特·安德森提供的数据,2004年太平洋顶峰投资公司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比2003年下降了20%。 “微利的三家电厂很特殊,都位于煤矿附近,受煤炭价格上涨影响小。”当然,由于发电厂投资额大,想收回全部的投资,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时间。目前太平洋顶峰的电厂离收回投资最快的至少还需要三年时间。 2004年,太平洋顶峰的CEO带领着手下的投资经理们,辗转奔波于中国北方的许多省市,考察了近40个项目,但是罗伯特却一直没敢进行投入。罗伯特观察到,处于严冬期的外资电力公司,此时出手,似乎是非常不明智的。 而且,太平洋顶峰的外资股东也质疑罗伯特,为什么其它企业已经撤出了中国,你们还不撤出。令罗伯特比较难堪。 罗伯特表示,由于自己的公司只在中国有投资,所以撤出中国就意味着全盘皆输,不像其它企业在其它国家也有投资,能进能退。 对于外资电厂来说,2004年的日子,没有几个过得很好,几乎全部亏损,或者接近亏损。其实,因为煤炭价格上涨而难受的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国内的企业也同样不好受,只有那些能够有效控制原材料成本的发电企业才能够获得不错的业绩表现。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能国际),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电国际)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是三家国内主要的国字号发电企业,但是由于控制煤价上涨的能力不同而呈现了不同的赢利能力。 去年7月份,三家企业公布了2004年中期财报,华电国际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下降了1.7%,而华能的净利润升幅也没有达到预期,仅为8.6%。这两家中国电力公司的股东们原本以为,中国强劲的能源需求会大幅提升公司利润,但他们忘记了原材料这一环,没想到煤炭价格的飙升对利润空间的打压如此之大。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是三家公司中表现最好的一家,原因是它能从邻近的内蒙古获得廉价的煤炭供应而受益,它的表现要好得多,中期净利润激增了42%。 大唐的发电厂集中在华北,供应的主要市场为北京和天津。这种集中的布局起到了帮助,并且由于电厂临近内蒙古的煤矿,使它在面对大幅攀升的运输成本时,所承担的压力相对较小。 大唐还和不少地方煤炭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它得以锁定80%煤炭供应的成本,这一比例在中国电力公司中是最高的。国家控制的煤炭合同价格要比现货价格低17%至50%。 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得大唐在上半年成功削减了单位燃料成本,是三家海外上市电力公司中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公司。 比起大唐,另外两家公司的日子可不好过。华能与华电的大多数电厂分别位于东部沿海及山东省,远离中国的煤炭产地。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北部和偏远的西部省份。 华能国际是上述三家上市公司中最大的一家,2004年上半年销售额达130亿元人民币。从上海到广东一带的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由于临近这一地区,华能国际一度受投资者青睐。 但随着煤炭价格扶摇直上,并突破公司对今年所作的5%的增幅预测,与地方煤矿缺少紧密联系的劣势抵消了高电价与需求上升带来的所有收益。2004年上半年,华能的单位燃料成本比上年同期上升了26%,公司因此受累。尽管销售增加了23.3%,但净利润仅增加8.6%,至25亿元人民币。 华电国际的形势更糟糕。其主要市场山东省是中国仅有的10个电力过剩省份之一,同时该公司为燃料多付出了14%的成本。 与各自赢利能力相匹配的是三家公司在香港市场上股价的不同表现。自2004年上半年,大唐的股价在香港上涨了13%;而华能的股价则下挫了13%;华电甚至跌去了31%。 背靠大树 虽然同样受到煤价上涨的困扰,但是外资电力公司与国有发电企业受到的困扰程度却不一样。原因是国有发电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统配煤的照顾,而很多中小外资发电企业却因为规模不够等原因,不得不更多地到市场买煤,从而无法有效控制成本的增加,价格上涨的冲击自然相差很大。 据方正证券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海介绍,每年一度的煤电交易会主要是解决大的国有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供求关系的,外资电厂参加不了大宗谈判。外资电厂规模比较小,煤从市场上采购的比较多,就要比所谓的统购煤贵了很多,而在国家电厂中,统购煤占了60%。 2004年12月29日,为了解决2005年电厂和煤炭生产企业之间大煤炭供应问题,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在秦皇岛召开了2005年度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议。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家电力集团副总向记者透露,截至1月7日18时,五大电力集团系统内所有电力企业共签下2000多万吨计划内电煤,虽然几大电厂仍然不够满意,但是起码今年发电用煤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保证,而那些外资电厂就要困难许多。这里所说的五大电力集团即指目前国内的五大电力集团: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和中电投。 即使同样是外资发电企业,也因为不同的合作伙伴而处境有所不同。“那些与国字号合作的外资电厂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它们也可以因为拥有强大的合作伙伴在煤炭供应方面,相对其他外资发电企业具备一定的优势。傍着大树好乘凉么!”袁海说。 “因为大的电厂有统配煤照顾,那些和五大电力集团合作的国外同行比我们强多了。”罗伯特·安德森对此有些不满。太平洋顶峰电力公司一直以收购地方小型热电企业为运营模式,自然无缘与“五大”展开“亲密”合作,“比起他们,我们的处境更难啊!” “我们希望政府能考虑热电环保的因素,让我们也加入到统配煤价格的行列中。”太平洋顶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共关系与集团沟通经理徐海虹向记者透露,缘于目前四亏三平的状况,该公司已开始考虑投资转移的可能,“目前正在考察一些小水电项目,至于具体如何,还不好说。” 在高峰时离开 如果无法控制因为煤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 对外资发电企业来说,撤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何时卖出,怎样才能卖个好的价钱则是很多希望撤离中国发电市场的外资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为周期性行业,中国电力行业如今还处在一个周期的波峰阶段,中国的电力需求强劲,而供给不足。而2006年则是业内普遍预计的中国电力市场供需平衡的年份,只要能在2006年之前卖出,一个好的转让价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对于外资出售旗下电厂的做法,《中国电力企业管理》杂志副主编张晓京就认为,在电力投资尚处在高峰期出售股权,对外资来说不失为明智选择。而邯峰电厂35.1亿人民币的转让价格也印证了身为外资电力公司的西门子选择此时出售,的确是做了一笔很合算的买卖。 从2003年开始,中国被认为开始进入一个重工业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时期, 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需求快速增加,中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电荒。工厂因此被迫停工,政府部门关闭空调,而拉闸限电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4个没有足够的电力来满足需求。 这种电力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很快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电力投资热潮,短短两年时间,数千亿人民币的资金投入到了电源建设上,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在2004年12月举办的北京首届能源投资研讨会上表示,2003年国家电力投资项目3500万千瓦(装机容量),2004年是4000万千瓦;而未经国家许可开工的则高达1.2亿千瓦。这种巨大的电力投资热潮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的电力投资正处在一种几近疯狂的无序状态,电源建设开始显得过度。 尽管如此,在未来两年中,中国政府仍将计划建设144家新电厂,新增装机容量为75千兆瓦。这应该差不多足以使供需平衡。但另外还有装机总量为250千兆瓦的电厂等待批建。其中在浙江和广东这些严重缺电的省份,许多电厂可能会先建后批。在浙江,许多工厂现在被迫每周停工3天。该省现已公开对抗中央的审批程序,并在积极推进25座新电厂的建设,其中许多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这种不顾一切的电力投资热潮的负面效应几乎可以肯定在两三年后显现出来:那时数十座崭新的发电厂可能竞相恳请客户光顾,而不象现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电站建成后要经过几年的运营才能盈利,许多外商都担心等到现在投资的发电项目进入盈利期后,却会碰上电力供过于求的时期,而造成亏损局面。于是在中国已经有项目的外方陆续撤离,没有项目的外方则继续观望,等待下一轮电力缺口的来临。 这种电力供需的大幅度波动还要归咎于低效的政府规划。当2003年开始出现全国范围的缺电状况时,低效的政府规划就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而倍受指责。中国2000年草拟的第10个五年计划涵盖2001年至2005年,根据该计划预测,电力消耗的年均增长率为6%,与1995年至1999年波谷期间的增长率相同。然而在该计划的前3年期间,实际的年均增长率几乎是预测数字的两倍,达11.8%。 计划制订者未能考虑到电力消费的波动性。工业用电占中国电力需求的四分之三,而所有消费量有四分之一来自四大行业:钢铁、铝、化工和建筑。所有这些行业都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这意味着,电力需求主要由易波动的国有企业投资周期所驱动,而不是由更稳定的消费需求增长所驱动。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工业需求急升,造成电力不足,并带来投资建设新电厂的浪潮。到90年代中期,电力消费增长开始减缓,导致电力过剩,电力购买协议被迫重新商定,以及新装机容量的缺乏。如今,我们又回到了周期性的90年代初那个阶段:电力严重不足,以及疯狂的追加投资。到2006年以后,几乎肯定会再次出现电力过剩、回报下降的局面。而现在距离2006年电力过剩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年的时间。 国企抢食 在中国电力市场上,行政干预几乎无处不在,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也让外资电力的生存发展始终处于国有电厂的围追堵截当中。 目前,国有电力占据国内90%左右的份额,外资和民营电力大概占10%。而国有电力中,国资委管理的五大发电集团占35%,地方发电集团占65%左右。 尽管国资已经在中国电力市场占据了绝对主力的地位,主要的新建电厂仍然由大型国有发电企业所垄断。2004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电力建设项目公告》,2004年国家批准新开工电站项目规模4000万千瓦,预计投产电站项目规模超过3700万千瓦。从公告显示,这些项目基本是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和中电投这5大电力集团申请的,多为其所属或占股份的大项目,5大集团外的中小型项目较少。 这种新增发电能力几乎全部被五大发电企业所瓜分的做法,使得中国电力行业中的五大集团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加强,“大者愈大,小者死亡”的国有资本垄断的形态正逐步形成。 尽管在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分拆时,国家曾经给五大发电集团划分过各个集团的发展领地。有关部门曾经有一个说法,任何一家发电集团在区域电力市场的发电份额,不应该超过当地总装机容量的20%。 但是,目前各大发电集团四面出击,竞相跑马圈地,已经超越了当时分配区域经营的限制。对于五大集团即将形成新的垄断的说法,五大发电集团中的一位人士辩称,即使五大发电集团目前联起手来,装机容量也不过全国总装机容量的35%,何况五大集团各有算盘,互相的竞争关系使他们各自保守秘密,沟通比较少,联合是不可能的。 但他同时也承认,一些地方抗风险较弱的发电企业,有可能会在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中,由于自身运营乏力,而可能投靠或者遭到更大集团的兼并收购,而“外资电力可能就是本轮洗牌中的大输家。” 外资的日子不好过,民营资本过得则更惨。由于电厂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民营企业虽然进入了该行业,但是投资数额一般只有几亿元,建设一些几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等。而这些正是国家清理的对象。 除了垄断新建电厂的权利,五大还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实力不断地通过并购的形式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并投资水电,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对于这一点,外资和民营因实力有限,再加上融资不畅也难以望其项背。 华能将从其母公司手中购买一座位于四川省的大型水电站,从而降低传统上对煤炭的依赖。与此同时,预计华能的母公司将与一家大型煤炭生产商合作,在安徽省投资建设一批火电厂。这个项目被称为“火电三峡”。华能也加入到大唐和华电的行列,探索投资煤矿和铁路网的机会,以降低整个供应链中的价格波动。 目前,很多以国有大电厂为主角的大型融资活动已在筹备中,其中包括中电国际和国电集团的海外上市计划,以及以上三家香港上市公司可能在国内发行A股的计划等。 电价改革 虽然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行政干预以及国有电厂的多重打压,但真正迫使外资电力企业裹足不前,甚至离开的原因是中国非市场化的电价制定体系,这一体系也一直是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争论焦点。 在中国,电价制定的现实情况是,形式上国家专责规划的部门国家发改委既制定向最终用户收取的零售电价,也制定电力分销商向电厂支付的批发电价。省级物价局有权批准价格变动,这种变动通常出现在发电厂与分销商签定的电力批发合约上。当电力需求猛增时,发电厂无法提高价格,除非政府授权提价。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被迫降低价格,比如在广东,这里比其它任何地区都更早经历电力短缺(在2002年夏季)。尽管如此,省级政府坚持实行既有计划,即削减电力价格,以维持广东省在吸引投资上的竞争力。 目前民用电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很大程度上由人为的工业用电高价来交叉补贴。其结果是,中国的工业电价远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这种一高一低的电价现状让政府在提高电价时感到左右为难。如果提高民用电价,害怕老百姓承受不起,特别是在中国的各种社会保险福利制度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保持民用电价的稳定,照顾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似乎已经是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的唯一选择;另外一方面,提高工业用电价格也是困难重重,原因是占全国用电四分之三的工业用电价格,与国际比较已经处在相对高位,如果再大幅提高价格,势必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的吸引力。 这样造成的最终后果是,中国电力行业的经济效益与它们应有的水平恰恰相反。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上,当需求高企时,发电企业通过提高电价而获得丰厚利润;再到供应过剩时期,它们用这些利润来为新电厂的建设提供资金,当需求高峰再现时这些新电厂就能发挥作用。在中国,发电厂无法在需求畅旺时获利,因而在供应过剩时期,只能靠关闭未使用的产能来保持现金流,而不是为下次需求高峰储备产能。只有当灾难降临时,新电厂才得以建设。 尽管苦难重重,中国电力规划部门也在努力采取措施减少煤炭价格狂涨与电价不能上涨之间的矛盾。 2004年12月15日,发改委发布了新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称,在半年内电煤价格上涨5%或超过5%,则相应半年后的上网电价也会做出调整。 对于新的煤电联动政策,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一些外资电力企业的不满。因为这会使电力企业承受30%的损失(发改委的意见规定,实行煤电价格联动时,将要求电力企业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在此基础上,将上网电价随煤炭价格变化调整)。太平洋顶峰就难以认同这样的政策。 “为什么30%要电厂来承担?作为一个投资商,都会作一个预算,如果成本上去了的话,利润渐渐就会少。我们没有看到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有这样的例子。原材料上涨,电厂却有责任去承担。”罗伯特·安德森说,“外商是放眼全球的,一旦看到中国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就会在决定投资之前多考虑一下了。” 除了太平洋顶峰外,一些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外商也对这一政策抱有疑虑。他们表示,该政策将可能以省为单位具体执行,各个省将在多长时间内,如何执行,会不会执行走样,或者拖后时间执行等等这些问题都不知道。 不仅是发电企业对这一政策感到不满,很多电力专家也并不认同,他们甚至认为,目前煤电联动可能是中国电力改革上的一种倒退。 “煤电联动政策与电价体制改革是背道而驰的。”袁海说,“电价又倒退到用成本推算的旧模式。如果长期实施这种政策的话,电价体制改革就遥遥无期了。” 外资企业看中的正是市场化的电价形成机制和市场化的煤炭价格机制。但现在的局面无疑会让不少外资企业失望。 “我们来中国已经八年了,可以说对中国电力行业的规定是非常熟悉的,如果说连我们都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那对于那些新的投资商就更不可能了。”太平洋顶峰投资公司CEO罗伯特·安德森如此认为。 罗伯特的话已经得到了证明。2004年8月, 中国宣布出售11座电厂,以筹集20亿美元用于改造国家电网,缓解长期的缺电现状。这些电厂共拥有6470兆瓦发电能力,主要位于中国中西北部和华东地区,是2002年国家电网公司成立时留下的少量发电能力的一部分。这些电厂在国内被认为是一些优质资产,并希望出售给国外投资者。但是从去年宣布出售到现在,半年过去了,没有一桩成交的消息传出。对此国外很多媒体给出的评价是中国电力监管体系不透明,过度的行政干预,电力行业的不可预测性,阻碍了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的意愿。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产经动态 > 《中国科技财富》2005 > 正文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