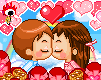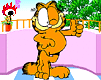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血气方刚的激进老头儿”江平:只向真理低头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 17:03 《Observer全球财经观察》杂志 | ||||||||||
|
围绕国际风云人物,专访身处影响力核心中的精英者,或是风格独帜的社会推动者。通过对话,展示一种人性张力、专业领域的权威性,直视他们影响社会的曲折进程。 江平的道德清单是:“诚实即牢记我就是我,他人不是我。试着在每一次混乱中找到最深处的核心并服从它,服从你辨认出的真理。”在参与的立法工作中,江平只对历史负责
江平被法学界称为中国民法“教父”,他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著名的民法学家。 1993年,《中国法学》杂志第1期,一篇题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的文章震动学界。文章提醒,1982年制订的宪法已实施10年,事关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一些重大观念问题还未能突破。而这一年,中国正经历着经济命运的转型。 在争论市场经济法律是否有“资”“社”之分的10年,新旧体制转型带来的观念冲突,几乎遍存每一部新法的诞生。《合同法》的起草中,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批评“草案”照抄国外和我国台湾的法条过多,对自己的经验研究不够。江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司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江平因此被评价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激进老头儿”。他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呐喊,我只对历史负责。”他的道德清单:“诚实即牢记我就是我,他人不是我。试着在每一次混乱中找到最深处的核心并服从它,服从你辨认出的真理。” “你爱江平什么呢?”当记者问江平先生的现任夫人崔琦,她的回答非常简单:“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我们是同一人格的人,如果不能互相同情,还能同情什么呢。在真诚相爱中,我看出了他有远大的理想。” 《全球财经观察》:您曾经有过很多头衔,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等,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江平:有人叫我江校长,有人叫我江主任,也有人叫我江教授,但更多的人叫我江老师。我觉得还是称呼我江老师最亲切。教授当然很好,很值得人们尊重,但终究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头衔。 《全球财经观察》:您原来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之后却从事了法学教育,是否有遗憾呢? 江平:新闻是我自己选择的志向,从1948年的情况看,觉得自己学新闻更能体现自由、平等的精神。新闻能为民请命,也能为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作出贡献。 参加工作后,我是国家组织安排第一批留苏学习法律的。按道理,那时候法律在中国并未得到很多重视,但无论如何,国家选择了一部分人专门去学法律,我当时也有一个很朴素的思想,觉得既然参加工作,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 但实际上,中国的法律从1957年之后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我们国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法律的虚无主义时期。我真正学会法律并能够得到应用,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全球财经观察》:这么多年,您觉得新闻和法律有共通的东西么? 江平:最大的共同点,是应该体现公平和正义。法律和新闻一样,应该有一个为民请命的思想。它虽然是强者制定,但它的真谛是公平和公正。法律与新闻都有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法制不足以包含民主,正像我们把民主与法制相提并论那样,那么法制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前提。 《全球财经观察》:您的学术思想,包括您追求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充满西方精神,燕京大学时的经历似乎比您的留苏经历,对您的影响更深。 江平:我从苏联学习回来后,遇上了国家的反右运动。从政治方面说,我应该没有问题,从历史说,我也是从地下的民主运动出来的,能够受到党的派遣去留学,经过了很多政治审查。当时很多人对我被划为右派,觉得奇怪。 后来人们找出原因,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当时的民主自由思想,前面会有一个前缀“资产阶级”。对于这个结论,当时我是很信服的。因为我确实一直都饱含着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当时参加的学生运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我们国家不仅富强,而且民主。富强在经济,民主在政治。但是,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相当长的时间,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一个对立面。现在看起来,这个观念当然是很差的了。 《全球财经观察》:1957年是您很悲痛的一年。您被打为“右派”,接下来是爱人的离开,之后的一次劳动事故中,您又失去了一条腿。那一年,您应该把这一辈子所能想到的事情都想过了吧? 江平:我想,这个波折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并不是个别人的。我们惟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的命运,恐怕是几十万人。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1957年对我是一场噩梦。但是,我想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能够经受这种挫折,如果你经历了,也可能就是大彻大悟,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这是我常常爱引用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再可以失去的,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全球财经观察》:但是,您的人格一直都没有失去。 江平:人格最重要的是独立。独立者,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当然,我顺境之后,又碰到过逆境,但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很大了。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条件,比起50年代末60年代几乎整个70年代要好很多。 所以,对于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建设,我始终是乐观的。这种乐观,不是一路顺风的乐观,而是说它在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与过去,已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建设,必然要走曲折的道路。我还是相信,现在中国总的情况是,进两步退一步。你如果老是在进步,这也不太可能,但是再往后退也不可能。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已不允许中国再倒退,不仅是经济改革上的倒退,也包括民主建设上的倒退。 《全球财经观察》: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是说您当时的信仰破灭了么? 江平:人的信仰应该这么看吧,总是要有所变化。我们当时学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但是我所经历的人生到七十多岁,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主义,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我们过去,年轻人想追求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一切都很美好,这个恐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一直在发展。真理都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活到现在,我只能说,我只会向真理低头。谁是真理,我接受谁。 《全球财经观察》:您会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真理呢? 江平:还是实践。如果在一个制度下,人们的生活实现了富裕,又实现了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大,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人们追求的不外两个,一是可以富裕起来,包括自由和民主,另外一个是不要悬殊太大,要和谐。 我现在也不盲目说美国多好,日本多好,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当然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落后的东西,但是,将来我们有可能搞得更好一些,更公平更发达一些。 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我很相信,社会也好个人也好,一种制度也好,都是在彼此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也可以说,社会也是达尔文主义。如果一个制度体现不出自己的优越性,那么它自然会被淘汰。 《全球财经观察》:在您最痛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死亡呢? 江平:我始终没有。在痛苦时,我曾考虑是不是不在这个社会生活,换另外一个。 改革开放后,我有了用武之地。上天给了我22年逆境,又给了我22年顺境。我在逆境中失去的时间,是27岁到49岁,正是一个人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创造一些东西的最好的时间,但是它可能换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很重要的是,我在逆境中仍然有寄托,我可以继续读一些书写一些诗词。人如果完全没有自己精神的寄托和某种理想,我想会是很痛苦的。 《全球财经观察》:您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研究间是否存在一个关系。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他会很注重道德的力量,也就会很认同自然法中的一些观点。您的人生经历,是不是会影响您的学术研究特别注重民主自由呢? 江平:这些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法律看成为一种工具。我的专业是民商法,所以在这个领域我很尊崇自然法学。 我在开始讲法律的时候,一再强调,法律在市场经济范围内,最根本的不应该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有任意性,而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应该更加有规律性,市场经济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竞争要符合竞争的规律。所以这个意义上,经济领域的法制首先要符合规律。 我本人主张,第一,要讲法律不能完全工具论,第二,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至于道德,法律本身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包含了一些道德因素的升华。比如我们常常讲的诚信原则,这已经是法制原则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道德,不管用什么词,它仍然包含一个道德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和道德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法律不能仅仅从道德角度看,他们的标准不是很一样。 《全球财经观察》: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处境一直是很尴尬,您觉得知识分子的良心应该保持在哪些地方呢? 江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知识分子由于他本身知识的背景、自己的能力,各个方面,任何国家包括我们古代,都是一个国家治国中很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能都靠没有任何知识文化的人来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多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们这样说,不是小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而是说,应该看到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有一个脊梁的作用。知识分子终究要有一个独立的判断,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他们的一个可贵作用,就是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避免造成决策上的失误。 《全球财经观察》:民商法属于私法,而您一直在关心宪政的问题,宪政属于公法,是社会现状要求您思考这个问题? 江平:根本理由就是一句话,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没有政治改革是下不去了,必然要引起断裂。这就是原因。我们现在上面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其实没有同步,现在是经济改革发展很快,政治制度改革很保守,但是没有这个改革是绝对不行的。 中国以后必然会有这样一个机构,叫宪法法院也好,叫宪法委员会也好,它会执行宪法诉讼。关于宪法审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方式的问题。基本上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宪法法院,中国现在领导层比较能够接受的,可能是宪法委员会 《全球财经观察》:您曾参与了《合同法》、《信托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等法律的制定,现在还在参与《物权法》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您觉得中国的立法环境是否有所变化? 江平:总的来说,比以前好一点,但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专家的意见有时候合适,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被采纳,我们也不能期望专家的意见都会被采纳。也许,学者和执政者的认识总有差距,学者往往要到达更理想的状态,而掌权者要考虑到稳定啊等方面,要考虑社会能否承受的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我想在您这个年龄,要保持思维上的清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平:我的身体和智力还可以,思维没有僵化和退化。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使自己的思想不要老化和退化。老化是不接受新鲜东西,退化是思维迟钝。我并不担心否认自己。 我这个人的爱好也很多,喜欢听京剧,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我最喜欢的还是贝多芬,在我困难时候,我能听到命运敲击的声音。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职业生涯 > 《OBSERVER全球财经观察》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