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解药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11日 11:04 《中国投资》 | |||||||||
|
○ 董小君 在刚刚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2005年,央行首次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也曾明确指出,我国金融业要注重防止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核心是防范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直接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金融风险,它隐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直接威胁着一国经济安全。 世界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反复证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安全最为危险的敌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31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考察表明,当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累计产出损失达到12%时,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1929~1932年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8218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5871亿美元,下降了29%;失业率从1929年的3%上升到1933年的25%;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 另据一项统计,从1980~1995年,共计65个国家经历了银行危机,在此期间,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挽救银行所支付的成本就高达2500亿美元,有近12次银行危机导致救助成本超过危机发生国GDP的10%。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为银行重新注资所花费的成本更加巨大,按公共部门为救助银行所花费的金额占GDP百分比计算,印度尼西亚为58%,泰国为30%,韩国为16%,马来西亚为10%。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人均国民财富水平倒退10年,使泰国国民财富损失近一半,使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降低一个百分点。日本90年代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一大批投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企业破产。企业资产价值的下降导致资不抵债。银行出现大量坏帐,也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危机问题。银行出于自救实行全面的收缩,撤回分支机构,收回放出的贷款,结果引起全国甚至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机理 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转变这一制度背景。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以保证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否寻求到这笔投资的来源就成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那么,我国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哪里? 首先是公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增长与金融剩余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2年、2003年迄今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几次经济过热时期,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61.8%。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意味着公有经济存在着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 在公有经济部门投资资金需求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对这笔金融剩余的动员,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其次是金融剩余动员的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依赖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当时的国家金融部门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会计部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公有经济部门的这种资本形成机制日趋解体。以“拨改贷”为特征的企业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的融资途径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国有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和聚集居民部门金融剩余的主要渠道。于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金融制度的核心特征”。 第三,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国家通过其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内的股票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社会金融剩余,然后通过倾斜性的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准入政策,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公有经济部门,这种转轨的思路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呈现双向累积的态势。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增加。从统计数字看, 转轨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基本都在60%以上,负债已由个别行业扩延到各个行业,由少数企业扩展到大多数企业,由短期负债扩展到长期负债,由过去的小额零星负债扩展到大额负债,由单纯的技改贷款扩延到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贷款。 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持续上升。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从1995年的22%上升到1999年的41%。近几年,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神奇地从2000年的34%下降到2005年的8.6%,连续5年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占比“双下降”。表面上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但是,有专家估计,经过两年的宏观调控,可能是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第三个高峰。在随后的2~3年,新增信贷将产生5%的不良率。 化解风险应从制度入手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中长期内的主要任务。鉴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产生于制度缺陷,所以,化解风险应从解决形成金融风险的制度因素方面入手。 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问题金融机构。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那么金融预警系统就是消防设备。在体系构建方法上,可以从微观、宏观及中间三个层次上来建立一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按照风险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不同档次,如很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和低风险。并可依据国际标准和我国实际情况,设定各档次的风险概率值,比如95%、75%、50%和15%。然后以各项指标数据乘以风险概率值,概算出从风险可能转化为危机的量化值。当然,这只是针对可以量化的风险,对于实际上难以量化的风险(如制度性风险以及政府干预导致的风险),只能进行专项披露和评估。 加强监管主体的协调沟通能力,完善“四位一体”综合监管系统。当前,我国在强化法定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同时,建立以“一行三会”为监管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监管。但是,“四大巨头”都是部级机构,彼此互不隶属。如何整合有限的金融监管资源,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构筑最后一道防线。第二,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增强协调磋商能力。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政府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行的领导轮流成为该委员会主席,每位主席任期1~2年,不得连任。第三,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目前,我国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各自建立一套信息体系,没有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难以做到信息共享。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要尽快建立反应灵敏、反馈及时、渠道畅通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 大力推进风险补偿制度,完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是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看,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有利于防止金融机构挤兑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从而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1)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人民银行对个人债务都实行保护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作后盾。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是造成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量居高不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鉴于我国已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我国应建立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在内的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2)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的一种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国际证监会组织将“保护投资者”列为对证券市场三大监管目标之一。我国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某些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造成大量资金黑洞所引发的赔付问题,以提高投资者信心,保持证券市场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投保者风险补偿机制。由于利差损失和投资失误等因素,人寿保险公司同样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寿险公司的倒闭会给投保人带来巨大损失,无疑会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目前,中国寿险公司(法人机构)越来越多,应当考虑择机建立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以形成规范的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强化自我约束机制:一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三是增加资本投入,降低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国有企业除了要求财政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投入资本金外,必须依靠直接融资方式面向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方式解决。 另一方面,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它。目前,我国有三家国有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这并不证明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就已成为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最多说明它们在制度创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中指出,银行坏账80%来自“非金融”领域。国外专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那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往往是金融管制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国政府管理金融理念,应由管制转为开放,由封闭转向透明,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现阶段,要合理划分政府职能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市场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金融市场事务而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习惯问题,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二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企业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不该管”的问题,这是理顺政府职能关系的核心。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银行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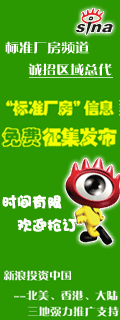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1.28万办厂年利100万 |
| 名人代言亲子装赚钱快 |
| 小女子开店50天赚30万 |
| 女人钱,怎么赚 (图) |
| 06年赚钱项目排行榜! |
| 介入教育事业年赚百万 |
| 我爱美丽招商!加盟! |
| 品牌折扣店!月赚30万 |
| 泌尿顽疾——大解放! |
| 拒绝结肠炎!! 图 |
| 颈椎病患者!我来晚了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发现!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